Main Points of Criminal Violation Judg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fied Legal Order
-
摘要:
法秩序统一是指国家现行所有部门法规范之间应当保持协调一致,要求一个部门法规定的合法行为,不应当被另一个部门法评价为违法行为,这是中国现代化法治进程中需要贯彻落实的重要原理。但基于不同部门法规范调整范围和任务的差异性,法秩序统一至今尚未得到实现。通过分析法秩序统一理论和违法关系论,对刑事违法性判断应当认可一种“缓和的”违法相对论。虽然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规范的后置法,但是刑法的后置性不意味着刑事违法性判断从属于前置法违法性判断。法秩序统一视角下的刑事违法性判断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刑事违法性判断基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整体独立,行为具备刑事违法性是指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而并非在前置法上被评价为违法。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前置法上合法是阻却刑事违法性的事由,具体表现为在构成要件该当性或违法性阶层发挥其“出罪”的功能和价值。
Abstract:The unity of legal order means that all current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coordinated and consistent, requiring that legal acts stipulated by one departmental law should not be evaluated as illegal acts by another departmental law. This is what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mportant principle.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pe and tasks of legal regulation adjustment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the unity of legal order has not been realized. By analyzing the unified theory of legal order and the theory of illegal relationship, a “moderated” theory of illegal relativity should be recognized for the judgment of criminal illegality. Although criminal law is a post-law of civi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and other legal norms, the post-law of criminal law does not mean that the judgment of criminal illegality is subordinate to the judgment of pre-law. The judgment of criminal illeg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fied legal order should b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The judgment of criminal illegality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independence of the three-level crime theory system. The behavior of criminal illegality means that it ha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is illegal, rather than being evaluated as illegal in the pre-requisite law.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gment of criminal illegality is relative, and the pre-legal legality is the reason for preventing criminal illegality,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incriminating” in the class that constitutes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r the illegality.
-
法秩序统一是指在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统领下,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各司其职,互相不产生矛盾,并最终形成整体的统一法秩序[1]212。而当不同社会关系被纳入不同部门法规范进行调整时,便会出现部门法之间的交叉关系。面对功能各异的部门法规范,实现法秩序统一要求正确处理不同部门法违法判断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就违法性判断应当坚持一元论还是多元论展开争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刑事违法性判断是对民法、行政法等前置部门法违法判断的补充,还是独立于前置法违法性判断之外,即刑法是作为第二位的后置法规范,对已具备前置法违法性的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还是与前置法处于平行关系,可以不拘泥于前置法规范而对行为的违法性进行独立的认定和判断。同时,学者们大多分析是否能够将民法、行政法上的违法性判断作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基础和前提,从而得出刑事违法性判断具有从属性或者独立性的结论。换言之,现有研究既鲜少关注部门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与违法性判断之间的关系所具有本质的不同,也往往忽视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上的合法能够成为阻却刑事违法性事由的重要功能。
据此,在厘清现有违法关系论学说局限性的基础上,区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同刑事违法性判断与其他部门法违法性判断之间的关系,将民法、行政法上合法所具有的阻却违法功能纳入违法性判断框架之下尤为重要。应当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和违法相对论中间寻找到进一步的折中与缓和,从而建构刑事违法性判断的方法论体系。一方面防止误将前置法上合法的行为评价为刑事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避免囿于前置法规范削弱刑法独立保障社会秩序之价值,从而不断靠近法秩序统一的理想状态。
一、 法秩序统一性及违法关系理论
(一) 法秩序统一性的理论界定
1. 德国的规范统一论
解决刑事违法性判断的难题,必须首先厘清法秩序统一原理所要求的协调模式。阿图尔·考夫曼曾说:“法的最终目标是提供行为规范,命令特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并对人的主观意志加以影响。”[2]法秩序中的各部门法规范都必须保持其一致性和统一性。因此,为了避免对同一行为同时发出准许和禁止的命令,德国学者普遍主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应要求各部门法规定都作出一致性的判断。
法秩序统一性的提出者恩吉施强调,法秩序中不应当存在任何相互矛盾之处,部门法规范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排除。“统一的违法性概念,即便是形式上的,也应当坚持,而各部门法中的违法性差异,无论如何应当逐步消除。”[3]因而,法律规范必然需要统一,民法、行政法上规定为违法的行为,刑法也应当确定其违法性。根据恩吉施的观点,汉斯·韦尔策尔进一步区分子“违法”与“不法”,提出了“违法性统一,不法性独立”的理论,认为不法是指违法行为自身的实体,而违法是一种纯粹的联系,是附着在不法之上的某种属性,即不法与法秩序之间的冲突,因此,特殊的刑法上的不法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一个统一的违法性;在不同法律领域中规定的所有禁止行为的构成要件,一旦有行为实现了其中之一,那么对整体法秩序来说,该行为就是违法的[4]。
总结而言,汉斯·韦尔策尔的理论认为,法秩序统一意味着民法上违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也应当评价为违法,但是刑事不法性的判断是独立于其他部门法而存在的。该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即在规范评价体系中,行为是违法行为与行为具有违法性,这两个命题并没有本质区别。将违法性与不法对立判断,模糊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违法认定的标准。并且,德国的规范统一论带有强烈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受到了命令说和纯粹法学派的影响。将违法性认定为对符合构成要件之举动的法秩序自身的无价值判断,法官至多只能去领会法秩序所作的不法评价,违法性评价的特殊性只是源于不同法域存在不同的构成要件而已。规范统一论坚持的是对法律规范本身的严格遵循,无视了法律制定本初的目的和实践中的灵活变通。法律不可能脱离实践和经验而存在,成为完全理性的逻辑产物。借助法律规范来实现其所期望调整之目的,才是法的核心。
2. 日本的目的统一论
不同于德国,日本刑法学界对法秩序统一的理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日本学者京藤哲久提出了目的论的统一论,即从法律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所要实现的目的出发,基于目的论的立场观察法律秩序和法律规范,法所要实现的目的以及采取的手段不应当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法的目的同样要求法秩序的统一性[5]145-160。因此,只要坚持法律规范目的的统一性,法律规范本身的矛盾之处便可以被理解。在合目的的基础上,各部门法规范可以设定不同的行为规范。当然,目的论的统一论不能容忍一切规范矛盾,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不能违反比例原则。法秩序统一性的目的统一论,为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依据。
日本目的统一论得到了中国部分学者的支持。例如,郑泽善承继了京藤哲久的观点,认为法秩序的统一性是合目的的统一[6];陈少青将合目的性统一认定为处理刑民法律效果冲突的基本原则,引入刑法补充性原则保障法秩序合目的性统一的实现[7];于改之认为,法秩序统一性应着眼于“目的—手段”关系的协调[8]92-94;汪昭武认为,应在容纳各个法域目的自主性的同时,坚持目的的协同一致性[9]178;简爱在“应然”的统一性立场上认为,法秩序统一性系法目的层面的统一,应当运用法解释学方法来降低规范冲突对法秩序统一性的破坏[10]。
总结而言,法秩序统一应当兼顾规范统一论与目的统一论。法秩序统一的基础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实践中落实法秩序统一应当重视目标的指引作用,以公平、正义、人权等法的价值作为基本理念,实现各个部门法规范之间的协调一致。
(二) 违法关系论的不同学说
1. 违法关系论学说概述
刑事违法性的判断问题,产生于对刑法与民法规范之间冲突协调的思考,继而拓展为对刑法同其他部门法规范之间违法性判断的体系性思考。违法关系论在理论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
① 。争论的焦点在于,刑事违法性是在整体法域中进行统一评价,还是根据不同法域进行个别判断[1]213。严格的违法一元论认为,根据各个部门法规范作出的违法性评价应当具有相同的结果,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违法性概念具有法体系一致性,因而不同法域必须对相同行为作相同的违法判断[11]。不论是破坏任何部门法规范,最终都是破坏了法秩序的统一性。因此,该学说不仅认为在其他部门法上被评价为合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也应当被评价为合法,而且认为在其他部门法上被评价为违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也应当被评价为违法。在其他部门法上被认定为违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不可能被认定为合法,刑法不能用其规范阻却其他部门法规范认定为违法的事由。各部门法规范之间的违法性判断互为充分必要条件[12]。完全否认刑法自有机制和独立功能的严格违法一元论,已经逐渐显示出其固有的弊端,因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放弃。
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认为,违法性判断在法秩序的整体当中是统一的,但是在形式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类别和轻重阶段[1]214,其他部门法规范的违法判断仅构成系争违法判断的必要条件[5]155。该学说肯定了“一般违法性”和“可罚的违法性”存在的必要性,在符合“一般违法性”的基础上满足“可罚的违法性”,即应当评价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一般违法性”,是不同法域共通的上位概念,是指因违反了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规范,因而具有整体法律规范上的“质”的违法性[9]174。 “可罚的违法性”,是指达到值得刑法制裁程度的“量”的违法性[13]186。具有“一般违法性”的行为,在没有达到可罚的程度之时,也不能具备刑事违法性,不能被评价为犯罪。“可罚的违法性”揭示出刑事违法性判断与其他部门法违法性判断的差异性在于,是否达到了可罚性判断的“量”的标准。成立刑事违法性,必须符合“可罚的违法性”这一层次的再判断[14]。
违法相对论首先肯定对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应当在法秩序层面上进行统一展开,但更侧重强调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15]80。法秩序的统一是必须被认可的,因为将民法、行政法上评价为合法的行为认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是不符合刑法设立的宗旨和目的的。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不同,违法相对论虽然支持“可罚的违法性”,赞同对法益的侵害需要达到值得刑法保护的程度的观点,但反对“一般违法性”的存在,认为刑事违法性判断没有必要从属于“一般违法性”的认定。先评价“一般违法性”,再判断“可罚的违法性”,不仅不符合司法实务中的做法,也不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基础,并不能对行为指引起到任何提升作用。肯定各部门法对违法性程度的判断存在差异性,需要进行相对判断[13]189,直接认定刑事违法性判断具有其优势性。
违法相对论否定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在其他法域被评价为合法,而违法多元论则直接否定了刑事违法性判断与其他部门法违法判断之间的关系。违法多元论认为,不同法律规范设立的目的具有根本差异性,违法性的判断也应当分别进行[16]。各部门法之间的违法性评价间相互独立,没有必然联系。因而,刑事违法性判断必须源自值得刑法处罚的实质违法性依据,而并非源自民事违法或者行政违法的前置评价[17]25。违法多元论不承认“可罚的违法性”,认为在承认“一般违法性”的基础上否认“可罚的违法性”,其效果明显弱于直接认定其不符合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使用“可罚的违法性”,反而削弱了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15]80,模糊了刑事违法性判断的依据和核心,减损了法律规范对行为人的直观指引和评价作用[17]204-205。当然,违法多元论也不排斥法秩序统一性的运用与实现。违法性判断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在整体法秩序下,应当尽量没有冲突[18]。然而违法性判断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必要绝对排除,只需要通过解释在合乎法秩序目的范围内保持一致即可[1]214。
2. 违法关系论学说评析
首先,违法多元论和严格的违法一元论弊端明显,显然不应当遵循。在民法、行政法上合法的行为,刑法一定不能评价为违法,这是法秩序统一最基本的要求。而违法多元论过分强调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不反对将民法上合法的行为认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是显然不合理的。同时,在民法、行政法上违法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部门法之间的违法性判断不必然保持严格的一致性。例如,在紧急避险情形下,如果坚持严格的违法一元论,行为人因紧急避险对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可能产生民法上的损害赔偿义务。以民法上的违法性为理由,限制刑法上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的紧急避险的成立范围,将因紧急避险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认定为刑事违法行为,显然不利于保障人权,存在扩大刑事处罚范围的风险。
其次,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虽获得了一批学者的支持,但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仍然秉持违法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作“定性”判断,刑法作为后置法作“定量”评价。而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并非由于该行为在民法或行政法上被评价为违法,而是由于其符合刑法上独立的规范目的的判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承认“一般违法性”的存在,要求刑事违法性判断必须以满足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中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迫使刑法放弃了独立的价值判断而成为其他部门法的附庸。刑事违法性判断本应注重“质”的判断而非“量”的评价,而“一般违法性”的存在将原本更加重要的对保护法益“质”的判断寄希望于维护私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民法和强调行政规范秩序的行政法,显然不利于刑法目的与功能的实现。对于紧急避险行为的认定,如果坚持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则应首先认定该行为具有民事违法性,符合“一般违法性”的前提,进而需要在“量”的基础上否认刑事违法性。而紧急避险在刑法上不被评价为违法,并非基于“量”上的损害程度没有达到值得刑法所保护的要求,而是该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正当利益基础[19]。再如,对于侵占不法原因给付之物,多数观点认为不构成侵占罪。不成立侵占罪的理由并非对不法给付进行“量”上的差异判断,从而认定其是否存在值得被评价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程度,而是基于给付者因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或强制法规定的不法给付行为本身丧失了民法上的返还请求权基础[20]。因为侵占罪保护的法益是给付人的返还请求权,不法原因给付阻却对受领人非法占有、拒不返还的评价,从而起到了阻却刑事违法性判断的效果。二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将“一般违法性”与“可罚的违法性”分开评价,判断路径复杂且不具有必要性。例如,盗窃1元钱的行为,根据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判断路径是:因为盗窃1元钱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因而在民法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也具有行政违法性,故而满足“一般违法性”的“质”的标准;因为盗窃金钱的数额只有1元钱,而刑法对普通盗窃的最低数额标准是1000元,故而该行为没有达到值得刑法处罚的“量”的标准,不具备“可罚的违法性”。综上所述,虽然该行为具备“一般违法性”,但不满足“可罚的违法性”,因此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违法相对论则认为,盗窃1元钱的行为,虽违反民法和行政法,但刑事违法性评价具有独立性。1元钱不满足“数额较大”的构成要件,因而直接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显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对比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和违法相对论两种判断途径可知,显然违法相对论思路更加清晰。同时,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提出的“一般违法性”和“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与一元论观点本身亦相矛盾。既然违法一元论追求法秩序的整体统一和一致性,那么不论是刑法还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规范,都应当得出相同的违法性判断,而不会出现刑法在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一般违法性”之上具有另一个所谓的“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法秩序评价存在不同层次的违法性,并未实现整体一致性。
综上所述,违法相对论在肯定刑事违法性判断相对独立的基础上,承认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上的合法行为不应当具有刑事违法性,相较于其他学说更具有合理性。但违法相对论过度强调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肯定“可罚的违法性”概念,以是否值得刑法处罚为前提判断刑事违法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予以修正。
第一,不仅“一般违法性”概念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可罚的违法性”概念也不具备规范基础和必要性。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并非“可罚的违法性”在中国刑法中的规范基础。王昭武认可“可罚的违法性”之存在具有必要性,认为将扒窃1.5元认定为盗窃罪是错误的,因为1.5元的数额并未达到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违法性最低标准,应当以《刑法》第13条“但书”作为法律依据阻却刑事违法性,给出的理由:一是扒窃1.5元数额较小,未达到值得刑法保护的“量”的要求;二是从一般民众角度出发,不会认为“小偷小摸”需要上升到动用刑法处罚的程度[9]187。然而,上述两个理由均存在缺陷:一方面,《刑法》并未规定扒窃金额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只要做出扒窃行为并获得具有客观价值的财物,即至少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成立盗窃罪;另一方面,一般民众观念中的“小偷小摸”只具备普通盗窃的性质,并不能认识到作为盗窃特殊类型的扒窃行为与人身关联度更高,对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侵害和威胁程度要远高于普通盗窃,故而《刑法》基于扒窃行为本身的高度社会危害性未对数额作出最低标准的规定。同时,如果直接运用《刑法》第13条“但书”阻却扒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则难以继续评价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无法进行综合准确的判断。设置扒窃犯罪的立法本意是威慑社会上日渐猖獗的扒窃行为,主要考量的是扒窃行为对人身权益的威胁和对公共安全的损害,而扒窃财物的价值只是次要的考虑因素。因此,不能武断认定扒窃1.5元钱的行为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而应当结合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综合判断[21]。扒窃1.5元钱的行为,仍然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鉴于数额较少,可以作盗窃未遂处理。同时,从根源上分析,《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只有在行为根本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前提下才能予以适用,是对可能被误认为构成犯罪的行为作概括排除,而并非阻却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原则性依据[22]。因此,满足《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即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而并非不以犯罪论处或不追究刑事责任。该行为根本不符合构成要件,而并非满足构成要件且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后再运用所谓的“可罚的违法性”认为其法益侵害性未达到值得刑法处罚的程度从而加以阻却。其次,“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存在重复判断之嫌。“可罚的违法性”判断的是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是否达到值得刑法处罚的程度,而这一判断本身就蕴含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评价之中。例如,盗窃1元钱的行为,本身就不满足构成要件中对于数额较大的认定,直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予以否定,不存在进入违法性阶层判断被侵犯的价值1元的财产权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同样,倘若盗窃数额为2 000元,即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又因不具有其他违法阻却事由,故而可直接评价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也无须再于违法性阶层对法益侵害的“量”进行二次评价。“可罚的违法性”的存在,不仅造成无必要的二次判断,而且会使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判断之间产生功能冲突和矛盾。再次,“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存在给违法性阶层的消极评价方式造成混乱[23]148。成要件该当性主要从正面积极判断行为是否满足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而违法性阶层主要从反面消极考察是否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承诺等违法阻却事由。而“可罚的违法性”这一概念,又要求从正面积极评价行为是否达到“可罚”的标准,显然与违法性阶层的消极评价方式相脱节,从而给违法性阶层的判断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第二,违法相对论将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评价为相互独立的平行状态,忽略了刑法与民法、行政法是后置法与前置法的关系,忽视了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规范上的合法性评价对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出罪”功能,仍然过度强调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总结而言,相较于其他三种观点,违法相对论更具有优势。应当基于违法相对性理论,结合刑法的后置性特征,在否定“可罚的违法性”和明确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规范“出罪”功能的基础上,演进出一种“缓和”的违法相对论观点。
二、 刑事违法性与其他部门法违法判断的关系
(一) 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规范具有后置法与前置法的关系
违法性判断过程离不开对法规范的适用,探究刑事违法性与其他部门法违法性判断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厘清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规范的后置法,这是由刑法的特征所决定的。
第一,刑法作为保障社会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屏障,其制裁手段具有严厉性,惩罚强度要强于其他部门法规范,包括剥夺行为人生命、自由、资格、财产等核心权益。因此,刑法不应当完全孤立于前置部门法而存在,否则刑法脱离重在强调救济和恢复的前置法规范直接加以最严厉的制裁,会破坏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安定性,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23]149。
第二,刑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刑法的调整范围涉及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秩序稳定、制度有序,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具体可划分至民法、商法、社会法、行政法等各个部门法领域。因此,涵盖多种部门法类型的刑法,应当关注各单一部门法规范中所规制的对象。
第三,刑法规范中存在大量概括性和兜底性条款,只重点规定了犯罪框架和量刑幅度,而对于具体行为概念的界定和犯罪构成的判断,仍需要借助民法、行政法等其他前置部门法规范进行解释。因此,仅参照刑法规范难以对刑事违法性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需要以前置部门法具体规范作为基础和参照。总结而言,刑法具有后置法的性质[24]27。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调整的是具有从属性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民法和行政法具有平行关系。而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后盾和屏障,其规定的自然犯和法定犯分别对民法和行政法规范进行回应。因而,刑法直面前置法规范,应当受到前置法规范的制约。
(二) 刑法的后置性不意味着刑事违法性判断从属于前置法违法性判断
虽然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后置法,但规范之间的关系与违法性判断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首先,法秩序统一要求刑法不能将前置法上合法的行为评价为违法,是对刑事违法性判断结果提出的要求和目标,而不是对刑事违法性判断路径进行干涉,施加起“定性”作用的前置性要求。刑法的后置性是针对刑法规范本身而言的,不是针对刑事违法性判断过程而言的。刑法是后置法是基于立法技术形成的客观事实,而刑事违法性判断是主客观结合的评价过程,两者具有本质差异。
其次,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前置部门法规范的功能作用和侧重点不同。要求基于不同侧重点和规范目的的前置法违法性判断成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基础和前提,是不具有合理性的。民法旨在修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着重评价行为的结果和责任,强调对损害结果的救济和赔偿,使之回复到原先的圆满状态。民法更强调责任而非违法问题,民事违法性不是民事不法行为的独立构成要件[25]。行政法旨在限制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个人的侵犯,侧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行政违法性表现为典型的行政不服从,是单纯的对行政法规范秩序的违反。行政违法性判断仅考察行为是否违反了行政法规范,而不以法益侵害为条件,较少关注主观评价阶层,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效率价值[26]。而刑法旨在惩罚犯罪,侧重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平等保护,着重评价行为本身的法益侵害性。刑法重视违法性判断,更多是出于谴责、惩罚和预防之需要[27],而不以补救损害为核心,要求主客观相结合,具有被动性、谦抑性的特征,更强调公平价值[28]。因此,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前置部门法相比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目的。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违法性判断同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关系并非存在“质”和“量”的关系,前者不会对后者产生根本性、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
同时,在形式上出现刑事违法性要求满足前置法违法,更多是源于前置法规范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和规范目的具有一致性[29]3,而并非刑事违法性判断后置性的体现。《刑法》分则虽然有部分条文规定需要援引其他部门法规范来认定犯罪,但并不意味着刑事违法性判断需要援引其他部门法规范的违法性判断。例如,交通肇事罪规定行为人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假药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加以认定,等等。这些规定是刑法作为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后置法的体现,而并非意味着应当据此认定刑事违法性判断从属于民事、行政违法性判断。违反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规范的事实提醒司法人员该行为违反刑法的可能性较大,并不表明可以不经过刑事违法性审查就直接将该行为认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基于规范目的的不同,刑法具有其独立的品格和特殊的调整手段,故而应当肯定刑事违法性判断具有其特殊的路径与方式。
(三) 刑事违法性判断不以前置法违法性判断为基础和前提
刑事违法性判断同其他部门法违法性判断是基于不同的判断路径,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基于不同的功能目的在划分概念范围和认定行为结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故而前置法违法性判断不能作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基础和前提。
首先,刑法具有其独立的品格和特殊的调整手段,与前置法在调整范围和概念界定上不必然保持一致。刑法规范中的部分法律概念和构成要件具有不同于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规范的含义,不应当作同一认定。行为在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所要求的“非法”或“违法”并不重合,因此,前置法违法性不是刑事违法性的充分条件,而是应当灵活运用各种解释方法、综合依据各类解释理由,进行目的论扩张或者限缩[8]94,结合不同法律规范所保护的具体法益进行具体认定和判断。例如,刑法和民法对于侵占的认定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侵占遗忘物具有刑事违法性,而侵占遗失物不具有刑事违法性。遗忘物是有意识地放于某处,因一时疏忽大意忘记拿走而暂时脱离控制的财物;遗失物则是意外丢失在某处,脱离控制处于无人占有状态的财物。遗忘物的范围要小于遗失物,侵占遗忘物的主观恶性和法益危害性也高于侵占相似价值的遗失物。中国刑法上只规定侵占遗忘物拒不返还构成侵占罪,而拒绝归还遗失物,不构成侵占罪,只能在民法上评价为具有违法性并追究其民事责任。刑法只将侵占遗忘物的行为评价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是因为侵占罪保护的法益是返还请求权[30],而遗失物已被丢失成为无人占有之物,侵占遗失物对失主法益的侵害程度要小于侵占遗忘物,故而刑法出于限缩侵占罪范围的考虑[24]37,不再保护失主对遗失物的返还请求权,而交由更加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的民法予以处理。刑事与民事违法性判断对于侵占认定的差异性,反映出刑事违法性判断具有其保护范围和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应当独立于前置法违法性判断进行单独考察。
其次,刑法与前置法对行为效力的承认方式和行为后果的规定方法并不相同。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上不承担责任和不利法律后果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了前置法的肯定从而具有正当性,可能存在前置法基于政策或其他考量不作要求,亦或者基于该部门法的保护目的并无需要承担责任的基础[23]149。因此,刑事违法性判断不能依赖前置法违法性的认定,而应考察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不被允许的侵害而作出独立的判断。例如,对于“事实婚姻”概念的效力问题,民法和刑法作出了不同的判断。民法不承认1994年2月1日之后的事实婚姻[31],因而,事实婚姻行为不能产生合法的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刑法则承认事实婚姻的存在,在未解除合法婚姻的前提下又与第三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具有刑事违法性,可以构成重婚罪。此时,对于“事实婚姻”概念的评价在民法和刑法上便出现了差异性,而这种概念上的相对性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原则,并非成为将具有民事违法性的行为评价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佐证。因为民法侧重保护权利义务关系,故而不赋予事实婚姻双方享有合法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作出对事实婚姻的否定评价;刑法则侧重保护法益,为了保护法定婚姻免遭事实婚姻的侵犯,必然需要肯定事实婚姻的社会危害性,即承认事实婚姻的存在,故而将事实婚姻纳入重婚罪的规制范围加以打击。民法和刑法都是为了反对第二次事实婚姻的存在,民法不承认事实婚姻构成重婚,本质上是对事实婚姻的否认;刑法承认事实婚姻可以构成重婚罪,本质上也是对事实婚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因此,民法和刑法的规定同样是对事实婚姻做否定性评价从而保护“一夫一妻”合法婚姻制度,在立法目的上保持一致性[8]102,是法秩序统一的体现。
三、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刑事违法判断的理论要点
(一) 刑事违法性判断基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整体独立
法秩序统一要求在认定刑事违法性时,应当考虑民法、行政法等其他前置法规范,民法、行政法上合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不能被评价为具有违法性[29]1。然而,不论行为在前置法上被如何评价,刑事违法性的认定最终都需要落到刑法对违法性的判断框架之下。因为法秩序统一是探寻合理的刑事违法性判断方法所期望达成的目的和效果,其本身并非作为合法或违法性事由而存在。即,不是因为坚持法秩序统一,故而前置法上的合法行为不能评价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而是为了实现法秩序统一,从而在刑事违法性判断进程中考虑前置部门法规范的存在。而刑法采用的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行为必须依次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才能具备刑事违法性。因此,基于法秩序统一,刑事违法性判断最终都是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落脚点,是整体独立的评价过程。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且不具备违法阻却事由的对法益造成侵害或危险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23]150。前置法上的违法不能直接成为认定刑事违法性的依据,前置法上的合法也不能阻断刑事违法性判断的进行。例如,虽然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求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但是并不意味着行政法上的违法性可以直接作为认定刑事违法性的依据。驾驶未经年检但并无故障的车辆正常行驶,遇行人横穿马路,躲避不及造成行人死亡,驾驶人不应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年检的目的是避免因车辆故障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事故并非由未将车辆进行年检的行政违法行为导致,而是由于被害人自陷风险。行政法上的违法性虽然在形式上具备违反法规的构成要件,但是该行为并不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行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并非行为人违反法规造成的,而是存在其横穿马路这一“介入因素”。同时,即使行为人即使年检也无法避免该危害结果的发生,被害人“自陷风险”的行为阻断了行为人违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该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该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并不依赖行政违法性的认定,而是遵循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的独立路径。
同时,独立进行刑事违法性判断也符合司法实践的客观实际。在司法实务中,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往往也不是先考察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在满足前置法违法性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判断是否达到刑事违法性的要求[32]。而是直接从构成要件该当性入手,逐一判断行为是否具备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在肯定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从而推定具备刑事违法性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从而得出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结论。
(二) 刑事违法性判断应当受前置法规范制约
如前所述,刑事违法性判断基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对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逐层考察,并不以前置法违法性为基础和前提,表现出“独立性”特征。但基于刑法的后置性地位和对法秩序统一的追求,刑事违法性判断显然无法仅依靠刑法规范得出结论,而势必受到前置法规范的制约。
第一,不能仅从违法独立性的角度考察刑事违法性。绝对独立的刑事违法性判断陷入违法多元论的误区,致使法秩序统一难以实现。一是刑法是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是国家权力最强烈体现的领域,相较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其社会成本也更巨大。因此,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特征,只有在通过民法、行政法难以有效保障权益的情形下才能动用刑法规范[33]。民法、行政法上评价为合法的行为,如果在刑法上评价为违法,则明显与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手段的补充性质不相符合,不利于实现对保障人权的要求。二是如果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规范评价为合法,而刑法作为后置法规范评价为违法,则向社会一般民众提供的行为规范内容产生混乱,破坏法的指引作用。行为符合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规范,却直接违反了具有后置性的刑法,不利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实现。三是基于比例原则要求[34],在刑事违法性判断过程中不能忽视行为是否具有前置法所赋予的正当权利基础,直接依据行为人单方的法益侵害要求承担最为严厉的刑事责任,而应在相冲突的法益间进行衡量,慎用刑事处罚。刑事制裁的后果常常是难以弥补和不可逆的,刑法的功能犹如双刃剑,必须理性判断权益损害的大小是否达到了有必要运用刑法规范加以保护的程度,运用刑法规范加以制裁的强度应当同所保护的法益相适应。刑法制裁具有强制力,如同药效强的药物通常伴有副作用,判断刑事违法性,必须慎重考察是否有必要动用刑法加以抑制[35]。刑法是控制违法行为所采取的最后手段,在有更加缓和的解决矛盾纠纷、保障法益和人权的方式时,不应当直接采用手段最为强硬、后果最为严重的刑事处罚。
第二,前置法规范对刑事违法性审查具有指导作用。一是刑事违法性判断需要考虑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所界定的违法范围大小。处罚范围的扩张或缩小,往往代表着立法者的目的期望,符合社会关系变化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刑法也应当同前置法保持一致,在前置法处罚范围发生变更的同时相应改变其违法性判断。二是刑事违法性判断应当关注前置法规范对法律关系的判断和对权利归属的确认[29]2。尤其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许多新型民事权利关系的定位处于尚无定论的模糊阶段。此时,刑法作为后置法,不应当武断地进行孤立的违法性判断,而应当综合各部门法规范的目的价值进行认定。三是刑事违法性判断不能忽视前置法对违法性判断的价值引导和功能定位。将前置法认为合法的行为认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是难以被社会一般民众所普遍接受的,刑事违法性判断需要受到前置法规范目的的制约。
(三) 前置法上合法是阻却刑事违法性的事由
前置法规范对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制约体现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并非绝对,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在前置法上不合法的行为才有可能具备刑事违法性,前置法规范上的合法化能够成为刑法上的出罪事由。介于刑事违法性判断是基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整体独立的一套方法,前置法规范上合法这一事由也必须被纳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之中,考察其是否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成立或为违法阻却事由形成正当权利基础,才能正确发挥其“出罪”的功能和价值。
第一,前置法上合法可以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行为必须符合刑法规范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才能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从而被推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构成要件是由多个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组成,其中一些构成要件要素不可避免会受到前置法规范的制约。例如,对于空白构成要件要素,其内容需要援引其他前置法规范进行确定[23]159。依据前置法规范判断行为是否具备这一构成要件要素,进而认定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前置法规范对刑事违法的判断具有间接影响。例如,刑法中有些罪名的规定以“非法”作为前缀,如非法拘禁罪,其中的“非法”便是指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要具备这一构成要件要素,该行为必须违反国家规定。故而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要求合法将公民予以羁押、医生基于防疫政策规定要求病人隔离观察等行为,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原因在于,上述行为存在前置法规范上的合法性事由,是“合法”剥夺他人身体活动自由的行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具备“非法”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不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进而不应当在刑法上评价为违法。又如,在酒店吃到变质食物,要求酒店方承担“巨额”赔偿,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行为人具有民事侵权赔偿的请求权基础;行为人从小偷那里窃回本人被小偷盗窃的财物,亦不成立盗窃罪,因为小偷临时的占有不能对抗本人的财产所有权。两种行为皆因存在民法上合法而不符合“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构成要件要素,进而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再如,以营利为目的,发行、销售彩票本应构成赌博罪,但基于财政政策的考量,行政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特定机构以特定形式发行彩票,因此这些特定机构便不再具备“违反国家规定”这一构成要件要素,进而能够运用行政合法阻却刑事违法性评价。并且,此处的“非法”与缓和违法一元论主张的“一般违法性”并不相同,不能认为非法拘禁行为符合“一般违法性”进而认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判断中的“非法”只是一项构成要件要素,并非作为前置法上的违法性评价而存在。
第二,前置法规范可以成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的合法性依据。正当防卫之所以能够成为违法阻却事由,并非因为其法益侵害性未达到值得刑法处罚的程度,而是因为行为人具有民法上的防卫权[24]32。在民法上,正当防卫尚且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刑法上更不应当被评价为违法。
前置法上合法可以分别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阶层成为阻却刑事违法性的事由,反之,前置法上的违法不能阻却刑事违法,不能为行为提供正当权利基础。例如,以恐吓、威胁手段索要“青春损失费”的行为,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青春损失费”违背公序良俗,并不具有民法上的请求权基础,故而索要行为并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敲诈勒索行为。但具有民法、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满足刑法构成要件,即使该种法律关系不为民法、行政法所认可或者规定为无效,与直接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大小亦是不同的。例如,基于“青春损失费”进行敲诈勒索的主观恶性一般认为小于直接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敲诈勒索第三人。因此,民法、行政法的违法性,可能成为评价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的依据,进而影响量刑时的判断。
四、 结论
违法关系理论呈现一元论与相对论对立的矛盾局面,源于对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和违法关系审查的误解。正确界定刑事违法性判断,应当首先明确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规范具有后置法与前置法的关系。但刑法的后置性不意味着刑事违法性判断从属于前置法违法性判断,刑事违法性判断不以前置法违法性判断为基础和前提。法秩序统一视角下的刑事违法性判断具有相对独立性,应当肯定一种“缓和的”违法相对论。其中,独立性体现为,刑事违法性判断具有其独立的规范目的,不依赖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判断,并非以民法、行政法上的违法性判断为基础和前提,而是有基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独立判断路径,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且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相对性体现为,基于刑法的后置法地位,刑事违法性判断受到前置法规范的制约,具体表现为前置法上合法是阻却刑事违法性的事由。各部门法虽具有不同的违法性判断路径,但理应求同存异,在统一规范目的的基础之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法益进行不同层面的保障。法秩序统一的实现任重而道远,离不开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只有正确进行刑事违法性判断,实现法秩序统一,才能发挥法的可预测性与指引作用,以促进法治体系化建设,维护公平正义。
注释:
① 违法关系论可以分为“违法一元论”(包括“严格的违法一元论”和“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和“违法多元论”。 -
[1] 曾根威彦. 刑法学基础[M]. 黎宏,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2] 阿图尔·考夫曼. 法律哲学[M]. 刘幸义,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150. [3] 陈少青. 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J]. 法学家, 2016(3): 16—29. [4] 汉斯·韦尔策尔. 目的行为论导论[M]. 陈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5. [5] 京藤哲久. 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J]. 王释锋, 译.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20, 7(1): 145—160. [6] 郑泽善. 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的相对性[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4): 60—70. [7] 陈少青. 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律效果论”之展开[J]. 法学研究, 2020, 42(4): 73—91. [8] 于改之. 法域冲突的排除:立场、规则与适用[J]. 中国法学, 2018(4): 84—104. [9] 王昭武. 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J]. 中外法学, 2015, 27(1): 170—197. [10] 简爱. 从“分野”到“融合” 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J]. 中外法学, 2019, 31(2): 433—454. [11] 陈金钊, 吴冬兴. 论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J]. 东岳论丛, 2021, 42(8): 162—172. [12] 杜里奥·帕多瓦尼: 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 注评版. 陈忠林,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4. [13] 山口厚. 刑法总论[M]. 3版. 付立庆,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4] 大冢仁. 刑法概说: 总论[M]. 冯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13. [15] 松宫孝明. 刑法总论讲义[M]. 4版补正版. 钱叶六,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6] 郭研. 部门法交叉视域下刑事违法性独立判断之提倡——兼论整体法秩序统一之否定[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 2020, 57(5): 76—87. [17] 前田雅英. 刑法总论讲义[M]. 6版. 曾文科,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8] 前田雅英.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研究[M].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2: 385. [19] 周光权. 论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J]. 政法论坛, 2021, 39(5): 38—53. [20] 王钢. 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J]. 中外法学, 2016, 28(4): 928—954. [21] 章桦. 扒窃入刑后的理性批判[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5(2): 65—78. [22] 张明楷. 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 中国法学, 2010(4): 49—69. [23] 张明楷. 刑法学[M]. 6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24] 陈兴良. 民法对刑法的影响与刑法对民法的回应[J]. 法商研究, 2021, 38(2): 26—43. [25] 时延安. 论刑事违法性判断与民事不法判断的关系[J]. 法学杂志, 2010, 31(1): 93—96. [26] 孙笑侠.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C]//山东省法学会. 依法治国专题研究——司法改革与依法治国理论研讨会、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52—59. [27] 刘宪权. 网络侵财犯罪刑法规制与定性的基本问题[J]. 中外法学, 2017, 29(4): 925—942. [28] 张绍谦. 试论行政犯中行政法规与刑事法规的关系——从著作权犯罪的“复制发行”说起[J]. 政治与法律, 2011(8): 40—50. [29] 周光权.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实践展开[J]. 法治社会, 2021(4): 1—12. [30] 柏浪涛. 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是返还请求权[J]. 法学, 2020(7): 130—143. [31] 王骏. 不法原因给付问题的刑民实像——以日本法为中心[J]. 法学论坛, 2013, 28(3): 140—147. [32] 王骏. 不同法域之间违法性判断的关系[J]. 法学论坛, 2019, 34(5): 64—77. [33] 佐伯仁志. 刑法总论的思之道·乐之道[M]. 于佳佳,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9. [34] 克劳斯·罗克辛.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J]. 蔡桂生, 译. 刑事法评论, 2010, 26(1): 265. [35] 西田典之. 日本刑法总论[M]. 2版. 王昭武, 刘明祥,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25—26.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55
- HTML全文浏览量: 95
- PDF下载量: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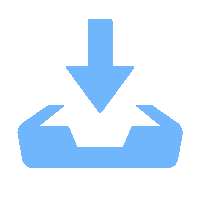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