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lu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Policy Makers: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Polic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
摘要:
政府数据开放是构建现代化治理能力和响应大数据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政策主体间形成协同网络更是消除数据鸿沟,提升数据价值的重要推力。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特征。研究发现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紧密度提升,整体网络经历了“核心-边缘”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演化特征,多中心协调均衡发展;网络个体“广度-强度”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核心度较高,核心主体地位趋向稳固;缺乏针对政府数据开放工作进行统筹协调的部门,存在网络稳定性较差、信息传递效率不高、权责匹配度低等问题,进而提出应明确协同主体间的利益和责任,并充分发挥核心主体的协调能力。
Abstract:Open government data is a key measure to build moder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respond to big data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formation of a collaborative network between policy entities is a driving force to eliminate the data gap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data.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government data open policy subject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cale of the network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its compactness has increased. The overall network has experienced structu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core-edge” to “core-semi-edge-edge”, and multi-center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network individual “breadth-strength” increased, financial The status of core entitie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ends to be stabl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poor network stability, low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low matching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poses to clarify the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ynergistic entit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ordination capabilities of core entities.
-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开放政府数据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的重要政策重点[1],当政府数据提供给公众时,公众可以检索、分析和整合政府数据与其他数据源,产生创新应用并创造对社会的新价值[2]。为了加速建设透明政府、提升营商环境、增强公众参与感和价值创造,各国相继发布了开放政府数据政策[3]。2009年,美国提出建设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成为最早开展政府数据开放行动的国家。此后,政府数据开放价值逐渐被挖掘,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欧盟以及国际组织将政府数据开放作为工作重点,制定了多样化的政策法规,为数据经济发展、数据价值发掘、数据治理提效提供了顶层指导和保障支撑[4]。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数据开放工作起步较晚,软、硬环境建设存在不足,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5]。结合世界范围内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推进以及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开始重视政府数据开放的经济、社会、治理红利,将其作为战略重点,出台一系列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和利用的政策[6]。相继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等政策,涉及国民经济、文化教育、公共安全、社会民生等多个重要领域[7]。政策体系的运行涉及对跨界问题的管理,必然会产生超越特定部门的职责权限[8],为合法合规解决跨界治理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9],在国家层面主要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由于不同政府部门具有各自的治理客体、治理目标以及治理手段[10],一定程度上造成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建立健全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制定主体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多主体协同的政策势能,提升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率,是对国家大数据战略的积极响应和建设现代化政府治理能力的顶层创新。因此,探索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制定主体的协同演化路径和演化规律,对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文献对于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体的研究较少,呈现零散化和碎片化,通常分散在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协同体系的讨论中。讨论一方面集中在政策协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上,如洪伟达在讨论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协同机理中,对政策协同主体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指出协同主体间存在横向部门联动不足、纵向政策落实缺少规制等问题[11]。Napoli等对美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对数据透明度作用力度进行研究,发现政策连贯性欠缺、一致性不足以及部门协调不畅导致出现责任分担的“真空地带”,数据开放程度远滞后于公众获取数据的需求[12]。还有部分学者对政策协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如Albano等运用组织间网络理论分析了开放政府数据的促进与激励因素,激励因素主要包括商业、法律、话语权、网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等优势[13]。迪莉娅从认知层面指出,政府工作人员对政策目标、工具以及实施的了解和评估也会影响部门间的协同[14]。还有学者提出推动政策协同的建议,如Yannoukakou等认为,深化政府数据开放有赖于明确的信息权责规定,成立特定的信息管理部门实施相关活动可以扩宽其传播路径[15]。毛子俊指出,应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进行顶层设计,协同构建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总体目标、确立数据开放的责任主体、统一数据开放标准与尺度、协同推进政策措施、构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模式[16]。少数学者对政策制定主体进行简单的描述分析,如陈玲通过政府公报对单独发文的央地政策制定主体进行分析,发现25个部门发文在5篇以上,75个部门发文在5篇以下,制定力度分布情况不高[17]。目前尚未有学者对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制定主体协同网络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归纳总结,对于政策协调网络的阶段如何划分以及不同主体在网络中的角色地位也有待挖掘。
因此,本文以国家层面的开放政府数据政策为样本,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并采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绘制政策制定主体协同网络拓扑图,从整体网络和网络个体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可知,“核心-边缘”是分析的基本模型[18],“广度-强度”是网络形态主要分析维度[19],因此,分别依据“核心-边缘”“广度-强度”的分析框架,识别出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和边缘节点,以及不同节点的演化规律和发展态势,总结协同网络的不足,为新时代国家大数据战略、数据经济发展以及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政策支撑。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SNA)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数学、通信科学等领域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研究分支。社会网络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关系论的思维方式[20]。社会网络分析法主要是分析网络的属性结构,研究数据之间的联系。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节点和各节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的集合[21],本文以政策制定主体为节点,两个主体共同参与政策制定为边,构建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制定主体协同网络。在整体层面,通过计算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网络密度、网络凝聚力指数、节点平均距离对网络结构的整体演化进行分析;在节点层面,通过计算节点的核心度,来分析主体在网络中处于何种地位,如核心地位、边缘地位等,并建立“广度—强度”二维框架对节点的角色演化进行刻画。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地方政策通常是对中央政策的延续和细化,中央政策更具有引领力和影响力[22],同时为保持数据层次的一致性,提升研究的针对性,本文选取中央政策进行分析。研究使用多源混合的数据收集方法,在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门户网站进行政策文件的查找,并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利用检索词“数据”“开放”“发布”“公开”进行组合搜索。收集到从1994—2021年间共146篇政策文本,并组织课题组的5位相关领域研究成员对收集的政策内容详读和整合,剔除失效政策样本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口岸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以及与研究内容关联度较低的样本如《国家统计局关于批准执行建设工程监理统计报表制度的函(2014)》。最终确定128篇国家层面政府开放数据政策样本最为分析的数据来源(样本结束时间为2021年10月5日)。
从政策效力角度来看,收集的样本中包括通知、意见、办法、公告、纲要、条例、规定、函、法律、决定、规划、方案等多种形式,如图1所示。其中,“通知”在政策文本中占比最高的为57.0%,是用于传达要求、告知执行的公文,使用频率高、形式灵活,因此具有明显的数量优势。“意见”相较其余文本类型占比也较高为14.1%,意见对下级部门的目标任务、执行规则提出了具体要求。结合“通知”和“意见”的占比情况可知,半数以上政策是政府有关部门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工作,进行相关工作中的告知、解读,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针对特定领域的具体文件数量较多,涉及到科技、交通、气象、地理、教育以及卫生等多领域,针对特定领域的具体性政策文件数量更多,而统领性、指导性文件数量偏少、高度不够,应出台更多纲领性文件完善政策体系。
(三) 样本阶段特征
从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发布时间看,中国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起源于1994年,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眠期,这期间相关政策的发布几乎为0。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有相关政策的发布,且2015年以后每年的政策发布数量都在7份以上,其中有五年超过了10份,2017年发布数量甚至达到了20份,政策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的指导不断加强。结合以上政策发布的时间与数量分布,以政府数据开放的标志性政策和特殊事件为时间节点,将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发布时间分布和阶段划分如图2所示,各阶段主体联合发文和单独发文数量如表1所示。
表 1 政策主体分阶段单独和联合发文数量表(前五名)阶段 形式 主体 数量 阶段样本占比 1994—2006年 联合发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 14.3%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1 14.3% 单独发文 国家统计局 1 14.3%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1 14.3% 国务院办公厅 1 14.3% 国务院 1 14.3% 中国人民银行 1 14.3% 2007—2014年 联合发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 3 11.5% 国家统计局 2 7.69% 财政部 1 3.85% 科技部 1 3.85% 中国科协 1 3.85% 单独发文 国家统计局 6 23.1% 国务院办公厅 3 11.5%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3 11.5% 国家文物局 2 7.69% 国务院 2 7.69% 2015—2021年 联合发文 财政部 6 6.32% 国务院 5 5.2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5 5.2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4.21% 中央网信办 3 3.16% 单独发文 国务院办公厅 16 16.8% 国务院 14 14.7% 国家统计局 7 7.37% 民政部 4 4.21% 教育部 3 3.16% 第一阶段,1994—2006年,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发布的萌芽期。1994年,国家测绘局为了提升地理信息数据的权威性和时效性,发布了《行政法规、规章和我国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发布办法》,对中国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发布主体、形式以及程序进行规定[23],对上述数据公布符合国际交往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此后,相关政策发布进入漫长的休眠期,2004年再次开始发布相关政策。这段时间政策发布数量整体较少仅有7份,所有的主体都是只发布1份文件,时间间隔也较长,政策还处于发展缓慢的萌芽期。
第二阶段,2007—2014年,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发布的开拓期。2007年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和范围、主动公开事宜、依申请公开事宜、监督和保障等进行了规定,建设透明、法制政府旨在发挥政府信息对社会生活的服务作用,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条例》的发布为各部门展开数据发布工作提供了指导,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先后发布数据公开和开放政策,尽管政策数量仍较少,但是保持每年都有相关政策出台。此阶段,政策数量增长到26份,国家统计局单独发文数量最多为6份,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数量最多为3份。此时期国家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拓期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不断将数据的开放向各个领域深入,过程艰难且效果不甚明显,但是却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为扩大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基础。
第三阶段,2015—2021年,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发布的加速期。201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应用为政府现代化治理赋能,为新时代政府治理革命带来挑战的同时更带来机遇,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范围和措施进行了规定,强调了社会公众在政府数据开放中的监督和价值创造作用。此后,政府数据治理在顶层设计中真正受到重视。随着国家战略调整、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各中央部门在对《纲要》的理解基础上发布各自的政策,如《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体育总局落实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等涉及交通、体育、互联网等各领域的政策文本。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和发展推动了政府数据开放实践和政策发布的加速发展,政策发布数量增长到95份,财政部联合发文数量最多为6份,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文数量最多为16份,此阶段的政策发布数量较前一阶段有了明显增长,在2016—2019年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期,并且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进一步推动政策发布的广度和深度。
三、 网络特征及分析
(一) 网络整体结构特征及演化分析
将本文收集到的128份政策文件,根据上文划分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发展三阶段,通过构建节点间n*n阶邻接矩阵,确定分阶段的政策制定主体协同网络。通过Ucient软件计算政策制定主体协同网络的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样本数量代表观察期政策发表的数量,网络规模代表观察期内政策制定主体的数量,网络关系数代表直接协同制定政策的两主体单次联结的总数,网络联结频次代表直接相连的两主体间协同制定政策的总次数,网络凝聚力指数表示的是主体之间协同的紧密程度,整体网络密度代表协同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联结数与最大可能存在的联结数的比值,节点平均距离表示所有节点最优途径的均值,用于衡量信息传递效率。
表 2 整体网络结构描述统计表指标 1994—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样本数量 7 26 95 网络规模 8 20 56 网络关系数 1 16 539 网络连接频次 1 16 557 网络凝聚力指数 0.036 0.072 0.320 整体网络密度 0.036 0.050 0.181 节点平均距离 1 1.595 1.835 为了深化对整体网络结构的认知,使用NetDraw软件绘制出三阶段的可视化网络拓扑图,如图3~图5所示。其中,图3(a)图是基于节点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代表出现的频次越高;图3(b)是基于度数中心度,节点越大代表直接与该节点协同制定政策的主体数量越多,该节点代表的主体越趋近网络的中心地位。
从宏观层面来看,政策发布数量不断增长,从第一阶段的7篇到第三阶段的95篇,增长了超12倍。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制定中来,政策和主体数量的增长都表明政府数据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宽,深度不断增强。网络关系数、网络联结频次、网络凝聚力指数和整体网络密度都不断增长,说明网络主体间的互动协同整体水平上升,但是数值整体都较低,仍是低水平的协同。节点平均距离不断上升,节点间信息传递效率变低,考虑是因为在网络构建初期,节点增加扩大了信息传递的覆盖范围,范围扩大导致的信息传递阻碍,超过了网络联结密度提升导致的信息传递便利[24]。这种情况下节点的增加则会降低传输效率,随着网络中节点增加趋向稳定,网络整体的效率也会趋于平稳。可见当前的政策协同网络还处于发展初期,稳定性还较低。
政策萌芽期(1994—2006年):此阶段共发布了7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政策制定主体为8个,联合发文主体为2个仅发文1份,数量较少,网络凝聚力指数和整体网络密度较低。此阶段网络关系数与连接频次数值相等,表明主体间的合作为一次性合作,没有建立频繁合作关系,网络是极其不稳定的。这一阶段的整体网络呈现出“涣散型”特征。
政策开拓期(2007—2014年):此阶段发布了26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政策制定主体增加到20个,网络关系数和联结频次也比前一阶段增长,说明政策制定主体在突破各种目标、利益的桎梏,展示出了更多的合作意愿和行动,网络凝聚力和密度也较前一期有所提升,虽然提升的不明显。但是此阶段与上一阶段类似,主体间的合作仍是一次性的合作,并没有多次的合作关系,网络的稳定性仍较低。此阶段的整体网络呈现“整体松散-个体集中”特征。
政策加速期(2015—2021年):此阶段发布了95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政策主体增加到56个,主体间的网络关系数和网络联结数较上一阶段呈几十倍的增长,协同主体更加多元化,网络凝聚力和密度也大幅增长,主体间联系更紧密。此阶段联结频次超过关系数,表明主体间开始倾向构建稳定的协同关系,而非单次合作,网络的稳定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此阶段网络呈现“整体扩大-多中心集聚”特征。
(二) 网络节点特征及演化分析
1. “广度-强度”二维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广度-强度”的框架,对政策主体在不同阶段内角色演化的二维分析进行直观展示。“广度”由主体直接联合其他主体的个数衡量,数量越高代表主体与其他主体协同能力越强;“强度”由主体直接联合其他主体的总次数衡量,数量越大说明与其他主体协同的频率越高。依据分析框架对应的数值矩阵,将政策制定主体分为“高广度-高强度”(HH)、“高广度-低强度”(HL)、“低广度-高强度”(LH)、“低广度-低强度”(LL)四种类型。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制定主体在协同网络中的角色地位如图6~图8所示。
通过观察图6~图8可知,网络中处于明显优势地位的主体数量越来越多,且中坚力量的主体数量也不断增加,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优势地位不断稳固。为明确各主体处于“广度-强度”四种类型中的哪一种,计算各阶段广度、强度的均值并进行划分。第一阶段的广度和强度的均值均为0.25,2个主体为HH型,6个主体为LL型;第二阶段的广度和强度均值均为0.75,7个主体为HH型,13个主体为LL型;第三阶段的广度均值为9.63,强度均值为9.95,29个主体为HH型,27个主体为LL型。可知,政策主体主要位于HH、LL型象限,且HH、LL型象限内主体变动也较大,大部分主体的角色还不明确。
2. 核心-边缘模型分析
对于HH、LL象限内主体在整体网络中地位的区别,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因此本文接下来采用核心度指标,对各主体在网络中的地位进行总体衡量。运用Ucinet核心-边缘连续模型,测算出三阶段内政策主体的核心度如表3所示。通常核心-边缘模型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类主体,核心主体在网络中通常扮演主导控制角色,与网络中的成员联系更为密切;边缘主体则是位于关系网络的边沿,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系较弱,在网络中的存在感较低;半边缘主体位于前两者中间,在网络中起到一定的衔接作用。通过此模型来分析政策制定主体网络整体网络结构以及个体在网络中核心度的演化。
表 3 整体网络节点核心度表(前8名)1994—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节点 核心度 节点 核心度 节点 核心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0.707 国家发展改革委 0.593 财政部 0.313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0.707 中国科协 0.56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311 国家统计局 0 科技部 0.56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0.305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0 财政部 0.56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0.268 国务院办公厅 0 国家统计局 0.233 科学技术部 0.206 国务院 0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0.23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0.189 中国人民银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 0.233 最高人民法院 0.189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0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0.02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0.189 将核心度小于0.05的主体定为边缘主体,0.05~0.1定为半边缘主体,核心度大于0.1的定位为核心主体[25],个体的位置分布如图6所示。第一阶段中核心主体有2个,边缘主体有7个;第二阶段核心主体有5个,边缘主体有15个;第三阶段核心主体有28个,半边缘主体有1个,边缘主体有27个。网络经历“核心-边缘”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演化特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心地位逐渐明确,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一直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
通过对比“广度-强度”二维框架模型与核心边缘模型发现,核心度高的主体其广度和强度也更高,两种模型的结果相为印证和补充。综合两个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更能有效说明个体在网络中角色的演化。
政策萌芽期(1994—2006年):这一阶段整体网络是比较分散的,多采用独立发文的形式,只有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文,两者对关于证券业第一次经济普查联合发布通知,是基于特定工作开展的协同工作。此时两协同主体处于坐标图(1,1)的位置,在观察期网络中为HH型,核心度为0.707,是网络的核心,其余的节点核心度均为0,为LL型。整体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
政策开拓期(2007—2014年):这一阶段,政策主体间的关系得到发展,新增了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协、财政部、科技部、水利部、海关总署等政策主体,政策主体在国家层面的覆盖面不断增强。国家统计局、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在两阶段均出现,且国家统计局的广度和强度较上一阶段有所增长,由上一阶段的LL型转变为HH型,在网络中逐渐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包括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协、财政部、科技部等在内的7个主体,其强度和广度数值虽较低,但是在观察期内处于HH型的角色,其余主体扮演LL型的角色。HH型主体中除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业及信息化部以外核心度值均大于0.1,为核心主体,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其余主体的核心度小于0.05,因此有15个主体处于网络的边缘地位,整体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
政策加速期(2015—2021年):这一阶段,政策制定主体间的协同发展迅速,这一阶段较前两个阶段新增了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网信办等政策制定主体,政策制定主体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制定中。在这一阶段中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29个主体属于HH型的地位,且财政部在“广度-强度”以及核心度数值两方面取代国家发改委,成为占据主导控制地位的主体,发挥着主要的协调作用。国家发改委虽然在这一阶段不再处于控制地位,但是其广度和强度都有大幅度增长,仍处于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此阶段HH型主体中除自然资源部以外,其余主体的核心度均大于0.1,处于核心地位,主要有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28个主体。自然资源部的核心度原来0.05~0.1,处于半边缘地位。核心度小于0.05的主体有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民政部等27个主体,处于边缘地位,整体网络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
综上可知,政策制定主体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政策主体间的协同效应也不断增强。且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协同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不断明确,在协调网络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体的广度和强度普遍得到提升,但是主体的强度与广度之比在前两阶段等于1,主体之间的合作是一次性的、不稳定的。在第三阶段中,部分主体强度与广度之比超过了1,主体间的协同更加频繁了。国务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制定政策5次,在协同网络中的关系是最稳定频繁的,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科学技术部的强度与广度之比也大于1,实现了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上也加强协作的频率,更趋向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 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逻辑
根据协同治理理论,多个组织之间进行资源信息整合、知识交流,并开展沟通与合作,政府数据开放领域的政策主体协同是主体间信息协同的主要表现。通过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体协同网络多阶段网络特征可以发现,协同网络的演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与中国政府治理透明化发展趋势以及大数据技术蓬勃发展相适应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主体间在数据不同生命周期,为实现数据共享和价值生成,产生了更为紧密和广泛的协同行为。TOE综合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灵活性以及可操作性[26],因此本文引用此框架考察组织-技术-环境因素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体协同网络的系统性影响。
组织因素。网络关系中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网络中协同组织建立的前提是主体的利益、资源以及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同网络的演化过程正是在主体间不断协调利益、共享资源以及统一目标的过程中建立的信任合作关系,这也是主体协同网络的内驱动力。随着我国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不断制度化、立法化以及程序化,使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对权责利的分配更为清晰,协同网络的稳定性不断被巩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公共决策透明性以及提升公众社会参与,实现政治和治理双重目标,也驱使协同网络不断演化。
技术因素。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体间协同不止意味着联合制定政策,同时意味着在后续的政策实施中彼此交换资源、共享信息、互相配合。信息技术是重要的整合工具,能够促进整合功能的发挥。信息技术对于实践工作具有深入的影响,能为协同网络中的主体互动更为紧密、关系更加有序、合作更有成效提供支撑。随着进入信息技术Web2.0时代,各部门的网站集约化建设和智能化终端建设不断加强,依托平台的不断完善,各部门实现数据流动和协同合作变成可能,且不断优化和完善。
环境因素。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发展的,公众对政府开放数据种类、数量、质量的要求不断上涨,公众需求成为主体协同的外部驱动力,只有扩展协同网络的广度和强度,增强跨部门的联合才能使得政府开放数据发挥价值。另外大数据产业发展也为政府开放数据政策主体协同提供了经济动力,政府作为最大的数据拥有者,但是部门间存在信息鸿沟,统计标准混乱,都会导致数据在被使用中无法发挥最大价值,只有加强部门间合作、实现信息的共享和开放,消除信息壁垒和失真,才能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因此大数据产业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主体协同,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主体间的协同。
四、 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研究结论
1. 整体网络紧密度提升,多中心协调均衡发展
观察整体协同网络,联合发布的政策和发文政策主体数量逐年增加,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拓展,从重点关注经济领域发展到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各领域,政府数据开放呈多样化倾向并在中央层面不断受到重视。主体协同网络的网络关系数、连接频次、凝聚力指数以及整体网络密度数值虽不高,但呈现上升趋势,政策主体间的协同效应越来越强,网络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节点平均距离的增加,意味着当前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协同网络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节点增加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效率,随着网络的不断稳定,节点的平均距离会不断降低。对网络主体核心度的测算发现,网络由前两阶段的“核心-边缘”结构发展为第三阶段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网络中出现起到重要的支持和连接作用的主体。且核心主体不断增加,网络呈现多中心性,说明网络由少数核心主体绝对控制主导变为多主体协调均衡发展。
2. 网络个体“广度-强度”提升,核心主体地位趋向稳固
观察协同网络节点,根据对政策发文主体的统计分析,单独发文的主体在网络中的比例不断降低,网络主体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可以发现,每一阶段都会有新的主体进入协同网络中,也存在上一阶段的主体消失在下一阶段网络中,可见政策制定主体的变动较大,政策的连贯性不高,主体间合作的稳定性有待提升。通过观察个体“广度-强度”二维矩阵发现,主体的广度和强度在前两阶段整体数值较低,随着2015年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第三阶段中开始出现广度和强度的高数值,如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广度和强度数值均在30左右。财政部虽不是发文最多的主体,但在网络中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控制的作用。因为随着政策工具的不断更新,相关政策已融合了强制命令型、经济刺激型以及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财政部对于各部门的资金支持作用越发重要。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历了“边缘跟随者-绝对控制者-核心协调者”的角色变换,其核心地位得到确认和稳固。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区别于科技创新、绿色经济以及国防安全等特定领域的政策,其覆盖面更加的广泛,因此,亟需更多的政策主体参与到协同网络中。
(二) 建议
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协同网络的整体网和节点分析发现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当前协同网络的稳定性较低,网络中每阶段都有退出的主体,这会导致政策失去连贯性、政策主体间的信息传递效率不高。其次,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总数逐年增加,但是每阶段单独发文的数量均远远高于联合发文数量,单独发文最多的主体在网络中却处于边缘地位,说明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和话语权分配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不利于建立协同关系和充分发挥主体的治理能力。最后,网络中扮演边缘角色的主体过多,无法接触网络的核心信息,边缘主体与核心主体在政策目标制定和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差异阻碍其合作,目前对于部门间合作的内部吸引力和外部驱动力仍不足。因此,为提升主体间的协同效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明确协同主体间的利益和责任。权责分配应遵循科学化、合理化以及相对公平的原则,增强网络稳定性的同时推动多主体朝均衡协调方向发展。应构建符合国家大数据战略发展要求的分工协同机制、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以及绩效考核机制,通过对政策目标的细化、政策工具的选择,明确财政、科技、交通等部门在联合制定政策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共同利益以及潜在阻碍,以免出现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间互相推诿、互不买账以及互相敷衍的政策“困局”,为政策制定主体的稳定合作提供执行层面的保障。另外,应保证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内容的针对性、时效性、连贯性以及一致性,各部门在政策制定中应统一规范用词,在发现政策文本冲突时应及时进行调整或修正,避免因领导班子更换导致协作中断。多主体协同中,加强对政策工具的应用,优化政策工具的选择及组合,确保政策工具可以有力支撑政策目标的实现,推动主体协同的广度和强度。
第二,充分发挥核心主体的协调能力。处于网络中权威地位的核心主体,应继续在联合、组织与主导其他主体参与合作中发力,加强主体间的紧密度。财政部作为网络中的主导主体,应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统筹,提升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技术支撑、人才保障、设施投入。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核心主体,起着全局规划和统筹管理的作用,对政府数据开放相关规划的制定应突出强调加强数据开放合作,运用政策工具鼓励合作行为。同时积极调动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政策主体,如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单独发文量较高的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这类主体具有较高的政策势能,将这类主体融入网络中,更有利于发挥相关政策的集聚、增值、辐射和自强作用,以及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落地和扩散。对于处于网络边缘且缺乏单独发文能力的主体,应通过内部鼓励和外部吸引联合的方法增强活跃度。
-
表 1 政策主体分阶段单独和联合发文数量表(前五名)
阶段 形式 主体 数量 阶段样本占比 1994—2006年 联合发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 14.3%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1 14.3% 单独发文 国家统计局 1 14.3%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1 14.3% 国务院办公厅 1 14.3% 国务院 1 14.3% 中国人民银行 1 14.3% 2007—2014年 联合发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 3 11.5% 国家统计局 2 7.69% 财政部 1 3.85% 科技部 1 3.85% 中国科协 1 3.85% 单独发文 国家统计局 6 23.1% 国务院办公厅 3 11.5%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3 11.5% 国家文物局 2 7.69% 国务院 2 7.69% 2015—2021年 联合发文 财政部 6 6.32% 国务院 5 5.2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5 5.2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4.21% 中央网信办 3 3.16% 单独发文 国务院办公厅 16 16.8% 国务院 14 14.7% 国家统计局 7 7.37% 民政部 4 4.21% 教育部 3 3.16% 表 2 整体网络结构描述统计表
指标 1994—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样本数量 7 26 95 网络规模 8 20 56 网络关系数 1 16 539 网络连接频次 1 16 557 网络凝聚力指数 0.036 0.072 0.320 整体网络密度 0.036 0.050 0.181 节点平均距离 1 1.595 1.835 表 3 整体网络节点核心度表(前8名)
1994—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节点 核心度 节点 核心度 节点 核心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0.707 国家发展改革委 0.593 财政部 0.313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0.707 中国科协 0.56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311 国家统计局 0 科技部 0.56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0.305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0 财政部 0.56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0.268 国务院办公厅 0 国家统计局 0.233 科学技术部 0.206 国务院 0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0.23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0.189 中国人民银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 0.233 最高人民法院 0.189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0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0.02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0.189 -
[1] 赵玉攀. 国内开放政府数据研究的系统评述[J]. 现代情报,2018,38(2):164—170. [2] KASSEN M. A promising phenomenon of open data:A case study of the Chicago open data project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3,30(4):508—513. doi: 10.1016/j.giq.2013.05.012
[3] 黄尹旭. 论国家与公共数据的法律关系[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3):27—31. [4] 丁红发,孟秋晴,王祥,等. 面向数据生命周期的政府数据开放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对策分析[J]. 情报杂志,2019,38(7):151—159.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7.023 [5] 吴金鹏,韩啸. 制度环境、府际竞争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扩散研究[J]. 现代情报,2019,39(3):77—85. doi: 10.3969/j.issn.1008-0821.2019.03.009 [6] 黄如花,温芳芳.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框架与内容: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17,61(20):12—25.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17.20.002 [7] 夏姚璜. 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的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研究[J]. 图书馆建设,2018(8):40—46,53. [8] 贾瑞雪. 中国个人信息治理政策主题和跨部门协同关系变迁研究[J]. 电子政务,2022(9):73—87. doi: 10.16582/j.cnki.dzzw.2022.09.007 [9] 洪伟达,马海群.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协同机理研究[J]. 情报科学,2020,38(5):126—131. doi: 10.13833/j.issn.1007-7634.2020.05.018 [10] 黄晓春,嵇欣. 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J]. 社会学研究,2014,29(6):98—123,244. doi: 10.19934/j.cnki.shxyj.2014.06.005 [11] 马海群,洪伟达.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协同的先导性研究[J]. 图书馆建设,2018(4):61—68. [12] NAPOLI P M,KARAGANIS J. On making public policy with publicly available data:The case of U. S. communications policymaking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0,27(4):384—391. doi: 10.1016/j.giq.2010.06.005
[13] ALBANO CS, REINHARD N. Open government data: Facilitating and motivating factors for coping with potential barriers in the brazilian context [J].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 2014(8653): 181—93.
[14] 迪莉娅. 政府数据开放成熟度模型研究[J]. 现代情报,2019,39(1):103—110. doi: 10.3969/j.issn.1008-0821.2019.01.013 [15] YANNOUKAKOU A,ARAKA I.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open government data synergy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47):332—340.
[16] 毛子骏,郑方,黄膺旭. 政策协同视阈下的政府数据开放研究[J]. 电子政务,2018(9):14—23. doi: 10.16582/j.cnki.dzzw.2018.09.002 [17] 陈玲,段尧清. 我国政府开放数据政策的实施现状和特点研究:基于政府公报文本的量化分析[J]. 情报学报,2020,39(7):698—709. [18] 刘正兵,刘静玉,何孝沛,等. 中原经济区城市空间联系及其网络格局分析——基于城际客运流[J]. 经济地理,2014,34(7):58—66. doi: 10.15957/j.cnki.jjdl.2014.07.039 [19] REAGANS R,MCEVILY B. Network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3,48(2):240—267. doi: 10.2307/3556658
[20] BONCHI F,CASTILLO C,GIONIS A,et 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 for business applications [J].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2011,2(3):1—37.
[21] LI N, HUANG Q, GE XY, et al.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EB/OL]. (2021-07-08) [2022-06-06]. https: //downloads.hindawi.com/journals/complexity/2021/6692210. pdf
[22] 吴宾,刘雯雯. 中国养老服务业政策文本量化研究(1994~2016年)[J]. 经济体制改革,2017(4):20—26. [23] 孟天广,张小劲. 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理论框架与模式创新[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18—25. [24] 刘纪达,董昌其,安实.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589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J]. 行政论坛,2022,29(02):98—109. doi: 10.3969/j.issn.1005-460X.2022.02.014 [25] 丛海彬,邹德玲,高博,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21,41(7):109—118.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7.012 [26] 丁依霞,徐倪妮,郭俊华. 基于TOE框架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电子政务,2020(1):103—113. doi: 10.16582/j.cnki.dzzw.2020.0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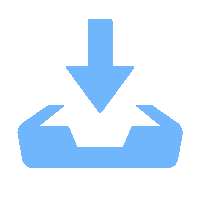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