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2022年10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即《北京公约》)的决定。《北京公约》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民航公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贡献智慧的国际法律文书。值此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全国各族人民迈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北京公约》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既彰显了中国民航法治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也为中国民航在疫情后的复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此,本刊特设《北京公约》专题,邀请来自民航主管部门及相关院校的三位长期负责、跟踪与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结合其多年的工作经历、研究心得以及对该公约获批后落地实施的思考,分别从该公约体系的更新、引渡条款的适用以及新增航空犯罪行为的罪名认定等方向进行撰稿,以期加深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北京公约》的认识,助力行业发展,加速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现代化成果在中国落地实施。 −杨彩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Convention System as a Result of the Beijing Convention
-
摘要:
《北京公约》将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运输危险物质等针对民航的非法干扰行为确定为犯罪,补充了三项管辖权,吸收了其他联合国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实现了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同时,在确立新的罪名、融合规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规定、妥善处理公约关系方面推动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且即将对中国生效。该公约的获批,对进一步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和维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 《北京公约》 /
- 非法干扰行为 /
- 管辖权 /
-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 /
- 反恐
Abstract:The Beijing Convention defines acts of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civil aviation, such as using aircraft as weapons and transporting dangerous substances, as crimes. And it has added three kinds of jurisdiction and absorbed the useful provisions from other United Nations anti-terrorism conventions, thus updating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conven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convention system by establishing new criminal acts, integrat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provisions of common law system and civil law system, and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vention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reviewed and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which will soon come into force in China. The ratif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air transport and safeguard the safety of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passengers.
-
2022年10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即《北京公约》)。《北京公约》于2010年9月10日制定,2018年7月1日生效,截至2022年10月20日,共有包括俄罗斯、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在内的45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北京公约》扩大了对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犯罪行为的刑事打击范围,提升了对民航安全的保护力度。该公约在制定后的8年里,共有22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随后4年,批准国数量又约翻了一番,达到45个。这充分说明,《北京公约》在更新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同时,有力推动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北京公约》的制定背景
(一)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构建
1. “反劫机三公约”奠定基础
国际民航组织(ICAO)自成立至今,一直将确保国际民航不受非法干扰作为目标。在国际民航组织的主持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航空安全的国际公约[1]。
1963年9月14日通过的《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及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即“1963年《东京公约》”),是首个国际航空保安公约。该公约确认了航空器登记国的刑事管辖权,赋予了机长重要的权力,并对非法劫持航空器进行了规定。同时,该公约确立的关于劫机的处理原则、降落地国义务等规定,也为后续其他公约提供了先例。但是,该公约并没有将具体的非法干扰行为确定为犯罪,也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实际行使管辖权,对于严重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劫机行为,该公约也没有制定具有执行力的措施。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评价,该公约好比一张渔网:网的面积很宽,但是网孔也很大;网嘴很大,但嘴里面没有牙齿[2]。
自1963年《东京公约》制定之后,在航空旅行越来越便利和频繁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劫机行为愈演愈烈,无论是劫机发生的次数还是受影响国家的数量都在增多。国际航空法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制定一部法律文书,确定劫机为国际犯罪,同时规定广泛的管辖权,确保劫机犯无处藏身,并将其绳之以法。因此,1970年12月16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即“1970年《海牙公约》”)获得通过。该公约除了规定劫机为犯罪并涵盖多种管辖权之外,还首次确立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为之后的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乃至整个国际刑法公约尤其是反恐公约制定了样板。
就在国际民航组织草拟1970年《海牙公约》之时,1970年2月21日,从苏黎世飞往特拉维夫的瑞士航空330号航班在起飞后不久,飞机上就发生了爆炸。机长努力实行紧急迫降未果,9名机组成员和38名乘客全部遇难[3]。这使得国际航空法学界进一步意识到,只有一部规制劫机行为的公约还不足以有效惩治各种危害民航安全的犯罪行为,还需要制定一部内容更加广泛的国际公约,将劫机以外的其他非法干扰行为同样确定为犯罪。于是,国际民航组织几乎同步筹划制定了“非法干扰民航安全(除劫持飞机以外的)公约”[4]25。不久,1971年9月23日《制止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即“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获得通过。该公约在1970年《海牙公约》有关规范劫机犯罪规定的基础上,对危害民航安全的其他种类的犯罪进行了规定。由于该公约所针对的犯罪大部分是地面上的犯罪,而公约所保护的飞机又不宜限制在“飞行中”的飞机,还应包括准备起飞或中途降停以及往返航程中降停的飞机[4]26。为了尽可能地涵盖各种情况的犯罪,在“门到门”的“飞行中”原则基础上,创造了“使用中”的概念,扩大了危害民航安全的各种行为的发生时间。这些行为包括: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或航空器从事暴力和破坏的行为,用任何方法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可能破坏航空器、危及飞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的行为等。
上述三部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又被称为“反劫机三公约”,是国际法与航空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为现代国际法与航空法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4]370。
2. 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和1991年《炸药探测公约》补充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恐怖分子针对民航的犯罪行为不再仅仅局限于航空器,其目标还瞄准了机场。为了弥补这一国际法上的缺陷,1988年2月24日通过了《制止在用于国际民用航空的机场内发生的非法暴力行为以补充1971年9月23日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的议定书》(以下简称“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该议定书将危害机场工作人员及机场运营设备的犯罪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并将受保护的航空器从“使用中”延伸至“未使用中”[5]。从1986年10月国际民航组织第26届大会有国家首次提出制定新的法律文书的动议,到1988年2月仅用16个月就完成起草并通过,再到1989年8月仅用18个月就得以生效,充分体现了各国对打击机场相关犯罪的共同意愿和决心。
1991年3月1日通过的《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探测的公约》(以下简称“1991年《炸药探测公约》”),通过在制造过程中添加该公约技术附件中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探测剂而使可塑炸药得到识别。此外,该公约还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当禁止和阻止在其领土上制造未添加识别剂的可塑炸药,禁止和阻止未添加识别剂的炸药运入或运出其领土,并对其所拥有的未添加识别剂的炸药的现有库存实施严格和有效的监管。1991年《炸药探测公约》通过对塑性炸药进行规制,表明了国际社会对炸机行为进行源头管控的努力,尽可能地避免了使用塑性炸药对航空运输进行犯罪的行为。
(二)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面临的挑战与相关工作的推进
在国际航空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截至20世纪末,上述五部法律文书共同构成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基本涵盖了针对民航的各种犯罪行为,规定了广泛的管辖权,并辅以“或起诉或引渡”原则,让实施犯罪行为的恐怖分子无所遁形。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意义上,构筑了航空保安的“天罗地网”。然而,这一切随着21世纪初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而发生了改变。
1. 国际民航面临多种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针对民航的非法干扰行为在方式和手段上都出现了原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在制定之初无法预料的新发展。其行为方式和手段皆融入了新技术因素并更加复杂和极端,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形式对社会危害更大、更加难以控制。除了航空犯罪的手段日益现代化之外,还出现了许多与航空运输活动有关的新的犯罪形式,如利用航空器运输危险物质、威胁实施航空犯罪、共谋协助实施航空犯罪等[6]。
国际民航组织经研究,确定了针对航空业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针对航空业的“新的威胁”,是指采用以前不认为会对民航业造成严重威胁的方式、行为或物品的行为;针对航空业的“正在出现的威胁”,是指设想可能被用于针对民航业的非法干扰行为,但尚未被采用或未被记载为采用过的方式、行为、物品。为了维护民航安全,有必要将上述行为在航空保安公约中确定为犯罪行为。
2. 原有管辖权已经不能全面覆盖犯罪行为
在管辖权的规定中,“反劫机三公约”虽然广泛确立了强制性管辖权和任择性管辖权,创造性地规定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但是实践证明仍然存有管辖权漏洞。事实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制裁,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宁愿承担出现管辖权积极冲突的风险,也在尽可能地避免管辖权空缺的现象,所以,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中的管辖权清单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长[7]。
但是,这种不断增加的管辖权清单仍然没有完全覆盖针对国际航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国际法中属人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的不断提升,有必要在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中继续落实这两种管辖权,如增加犯罪行为人的国籍国和犯罪行为对象的国籍国这两种属人管辖权。另外,随着管辖权的增加,还应该对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予以规定。
3. 其他反恐公约不断更新发展
“反劫机三公约”开创了国际反恐公约的先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航反恐公约在国际反恐公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民航领域之外的国际反恐公约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得到了较大发展,如《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等。这些新的反恐公约结合国际反恐形式,无论在罪名确定、管辖权扩展,还是在军事活动例外等方面,都进一步丰富了内容,填补了空白。近20年来都没有进行更新的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已显得日益脱离时代,有必要尽快更新。
4. 国际民航组织积极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里,国际民航组织面对国际航空保安体系中存在的不足,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公约修订的问卷征集。2001年10月,国际民航组织第33届大会第A33-1号决议,要求其理事会和秘书长采取紧急行动,审查现行航空保安公约是否可以充分处理针对民航的新的威胁。2002年6月,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批准了国际民航组织航空保安行动计划。其中,项目12是对已有航空保安法律文书进行审查,查明在涵盖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方面所存在的空白和不足。2005年3月,国际民航组织向各缔约国发出“关于修订现有航空保安的国际航空法文书必要性的问卷”,征求各缔约国对修订现行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意见。54个国家进行了答复,绝大多数国家表示现行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存在不足,应予以修订。二是积极起草公约文本。在完成问卷征集之后,2006年2月,国际民航组织设立专家研究组,协助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起草涵盖针对航空业新型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书。2007年3月,在专家研究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设立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委员会,起草一份或多份“处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针对民航威胁的法律文书草案”。2009年9月,在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法律委员会对有关重点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对公约草案做了进一步修改。三是召集外交大会审核《北京公约》。《北京公约》草案完成后,2010年8月,国际民航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大会(以下简称“北京外交大会”),就重点问题、草案文本以及修订文书的形式等进行最后的讨论和修改,最终通过了《北京公约》。《北京公约》确立了针对民航的新的犯罪行为,扩展了新的管辖权,吸取了其他反恐公约的有益规定,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 《北京公约》推动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完善
《北京公约》共25条,其中12条为新增或是对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进行修订的条款,主要包括增加了新的犯罪种类,修改或新增相关定义,扩展了管辖权,以及吸收其他国际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等。
(一) 新增和完善了九种犯罪行为
将相关行为确定为犯罪,是修订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初衷,因此,《北京公约》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最为重要的就是新增了九种犯罪行为。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共两款,共规定了七种犯罪行为。《北京公约》在修订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时,除了纳入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规定的犯罪行为之外,还采用了三种方式,新增和完善了九种犯罪行为:一是在第1条原有两款内容中补充了若干新的犯罪行为;二是在第1条原有两款内容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两款,规定了新的犯罪行为;三是补充了新的定义以完善原有的犯罪行为。
1. 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
“9·11”恐怖袭击事件本身是多种犯罪行为的聚合,如劫持飞行中的航空器,故意损坏使用中的航空器,在飞机上使用暴力、谋杀以及其他导致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犯罪行为[8]59。这些犯罪行为中,有些是原有航空保安公约已经规定的罪名(如劫机),有些是刑法体系中的一般罪名(如谋杀),虽然可以按照这些罪名逐一定罪,但是不能突出“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作为武器”这一犯罪特征,更不能突出这种犯罪行为的恶劣性和社会危害性。因此,《北京公约》中首先增加了“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这种罪名,这是国际航空法学界对类似“9·11”恐怖袭击事件等犯罪行为在法律上的回应,表现出了国际航空界不容忍此种恐怖行为的决心。
2. 使用航空器传播危险物质
与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这种犯罪行为类似,使用航空器传播危险物质的犯罪分子也是将航空器作为犯罪工具;但不同于前者将航空器本身作为武器来进行攻击,后者则是将航空器作为传播危险物质的犯罪工具,而危险物质包括生化核武器以及其他爆炸性或放射性物质。
3. 使用危险物质对航空器进行攻击
使用危险物质对航空器进行攻击的犯罪行为,不再将航空器作为实施犯罪的工具,而是作为实施犯罪的目标。从攻击方向上来看,这种攻击既包括从航空器外部对航空器进行的攻击,也包括从航空器内部发起的攻击;从攻击手段上来看,这种攻击既包括生化核武器,也包括爆炸性或放射性物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攻击,尤其是从航空器内部发起的攻击,即使未对航空器本身造成损害,但只要造成了机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破坏,同样构成该罪。
4. 运输危险物质
这是一条自提出起草动议就伴随着争论的条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是否超越了“民航安全”的限度、是否与其他公约类似规定保持统一,以及是否明确了行为人的“知情条件”[9]。在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讨论之前的阶段,一种观点认为,应将运输危险物质确定为犯罪,依据是《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已经在海上运输领域确定了类似行为是犯罪,如果航空运输领域没有禁止同类行为,就会形成法律体系的空白或缺陷;另一种观点认为,仅仅运输危险物质与民航安全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不应当在民航公约中将其确定为犯罪①。
至北京外交大会之前,各方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应当将运输危险物质确定为犯罪,否则将会影响民航安全。但是,此时争论的焦点在于确定该罪的主观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明知其所运输的物质将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时,才构成犯罪;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否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只要非法和故意运输危险物质都应被定为犯罪②。由此可见,前者侧重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而后者侧重防止危险物质,尤其是生化核武器的扩散。
最终,在多方协调之下形成的案文规定,恐怖主义目的是构成爆炸性或放射性物质运输罪的要件,但不是构成生化核武器运输罪的要件。同时,在该项最后增加了特别规定,即只要当事国符合多边不扩散等条约的规定,那么某些行为则不适用该公约。
5. 组织或指挥犯罪
与前四种新增罪名类似,《北京公约》在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4款中新增了组织或指挥犯罪这一罪名。这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所代表的典型情况,恐怖主义行为的现场实施者,即该事件中劫持航空器撞向地面目标的恐怖分子,都在这场恐怖袭击中死亡,也就无法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该事件真正的幕后组织者,即组织或指挥犯罪的人却逍遥法外;而且,现代恐怖行为,多为特定组织统一策划,追究这些幕后组织或指挥者的刑事责任往往更为迫切,也可以尽量避免后续类似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6. 协助逃匿
在《北京公约》起草过程中,曾有国家希望将运送逃犯确定为新的罪名,但遭到了部分国家和航空公司代表的反对。经过进一步协商讨论,最终在第1条第4款中新增了将协助逃匿行为确定为犯罪。实际上不仅将运送逃犯这种典型行为,而且将协助他人逃避该公约相关罪名的调查、起诉或惩罚的各种行为均确定为犯罪。但是,这种行为必须是非法和故意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实施的有关行为不构成该罪。同时,《北京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国内法特殊规定的例外条款。
7. 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
不同于上述六种在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1款或第4款内新增的罪名,《北京公约》第1条专门新增了一款罪名,即将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确定为犯罪,具体包括了威胁实施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确立的四种犯罪行为、《北京公约》新增的三种犯罪行为。
《北京公约》确定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时还注意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该罪并未直接要求危及航空安全,但实际上,威胁要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是危及或可能危及航空安全的犯罪行为。二是威胁应当是可信的,区别于编造的或是虚假的威胁,这其实也正是未将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确立的传播虚假信息纳入威胁范围之内的原因。至于可信的定义,《北京公约》本身并没有规定,而是交由管辖法院根据不同案件的特殊情况来进行个案解释。
8. 共谋或商定犯罪
与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类似,共谋或商定犯罪也是《北京公约》单独新增的一款罪名。共谋是指2人以上为了实施特定的犯罪而进行的谋议,可能是策划实施犯罪,也可能是商讨如何实施犯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0]175。源于普通法的“共谋罪”,其基本理念是只要行为人就不法行为的实施达成合意,共谋行为本身即具有可罚性,就是一种犯罪[11]。共谋罪的成立并不需要行为人继续推进共谋将共谋罪的目标行为实施完毕,甚至根本不需要实施任何外化行为[10]175。因此,《北京公约》明确规定“不论是否实际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相关罪行,均成立该罪。
9. 网络攻击空中航行设施
不同于前面八种在《北京公约》中直接新增的罪名,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1款第4项已将破坏空中航行设施确定为犯罪。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新技术手段扰乱航空秩序,危及航空人员、乘客和航空器的安全,如使用无线电发射器或其他手段干扰或改变地面或机载的航线或导航控制系统状态,或者篡改与航空运行相关的计算机数据等[8]64。因此,《北京公约》没有修改已有的罪名,而是在第2条中新增了空中航行设施的定义,纳入航空器航行所必需的信号、数据、信息或系统。如此一来,原有的破坏空中航行设施,既包括物理攻击,还包括网络攻击。
(二) 扩展了管辖权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已经包含了较为广泛的管辖权,同时辅以“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当时的国际法环境下,基本能够覆盖各种情形。但是,《北京公约》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其他反恐公约的有益规定,继续扩展了三项管辖权,包括一项强制性管辖权,即犯罪由该国国民实施,以及两项任择性管辖权,即犯罪是针对该国国民实施和犯罪由其惯常居所在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实施。总体来看,这三项管辖权都是国籍国管辖权的体现,无论是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还是受害人的国籍国,一般来说,无国籍人居住地所在国也是无国籍人确立国籍的一种方式。这种规定的核心是属人管辖和保护性管辖在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中的又一次强化。公约缔约国作为国籍国,有了更大的行使管辖权的机会和依据。这一修改加大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航空犯罪的管辖机会,使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都没有了藏身之所,强化了对国际航空犯罪的追诉[12]。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上述诸种管辖权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但各国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个案协商的方法来予以解决。从弥补原有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空白,堵住犯罪嫌疑人逃避惩罚的漏洞,布下“天罗地网”的角度来看,《北京公约》扩展的管辖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 补充了其他有益规定
从“反劫机三公约”到“9·11”恐怖袭击事件,虽然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补充了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和1991年《炸药探测公约》,但是其他国际反恐公约的发展还是快于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发展。因此,在《北京公约》制定过程中,也注意吸收了其他反恐公约的有益规定,包括政治犯不例外、军事活动排除条款、公平待遇条款、法人实体犯罪等,下文仅以前两者为例来进行论述。
1. 政治犯不例外条款
政治犯不引渡是指国家对于因政治原因而遭受外国追诉的外国人不予引渡,是一项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基于尊重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权。但是,由于政治犯或政治犯罪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加上各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有些国家内部未对引渡作出明确定义,所以,各国尚未对政治犯罪的定义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政治犯不引渡作为引渡制度的例外,一旦滥用,将会导致某些犯罪人利用该原则来进行法律规避从而逃避法律责任,甚至会打破维护国际公共秩序和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原则进行限制,以防止其被滥用,从而维护国际公共秩序。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对几类犯罪中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中一类即恐怖主义犯罪,早期成果体现为1977年1月27日签订的《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所创设的政治犯不引渡的例外。这一“例外中的例外”原则,使政治犯或政治犯罪的概念大幅度缩小,随后的反恐公约普遍引入了政治犯不例外的条款,明确不得将公约规定的罪行视为政治犯罪。
《北京公约》吸收了以往反恐公约的规定,确认了政治犯不例外条款,政治动机不再是缔约国拒绝引渡或拒绝提供司法协助的理由,能够有力震慑针对民航的犯罪行为。同时,为了防止政治犯不例外条款完全排除原有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对国际法已有的体系造成冲击,《北京公约》还规定了一条配套的保障条款,实质上是一项对缔约国引渡或司法协助义务的例外。该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犯罪分子的合法利益,防止缔约国滥用政治犯不例外条款;另一方面,明确了《北京公约》没有给缔约国强加引渡义务,缔约国可以援引该条款,拒绝引渡或提供司法协助。
2. 军事活动排除条款
军事活动排除条款也是20世纪末以来制定的反恐公约中普遍加入的条款,但在《北京公约》起草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国家认为,公约应当约束“一国军事部队为执行公务而进行的活动”,避免让某些国家的非法干扰行为合法化。因此,这些国家主张直接删除第2款。其他国家则认为,《北京公约》重点规范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的活动,而且这一条款已被以往多部反恐公约采纳并执行,因此建议保留②。实际上,这已不仅是国际法问题,而是涉及政治问题,尤其是所谓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与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之争,十分敏感。最终,《北京公约》除了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相关规定加入第1款之外,对军事活动排除条款的其他内容,皆是从其他已经制定的反恐公约中逐句引用,未做更改。
(四) 推进多方面的法律创新
《北京公约》在确立新的罪名、扩展管辖权、协调公约间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更新,这些内容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首次将威胁本身规定为犯罪
原有的航空保安公约并未将纯“威胁”本身界定为犯罪,但在实践中,一些针对民航的威胁行为,本身就具有危害民航安全的性质,甚至会危害民航以外的公共安全。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虽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完成犯罪,但是也可能对民航安全造成重大不利后果。《北京公约》在借鉴《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中关于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民航特点,确立了威胁犯罪,弥补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空白,尤其是可以有效预防针对民航的犯罪行为。
2. 融合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进行规范
共谋或商定犯罪在《北京公约》中予以确立,是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一项创新,尤其对犯罪预备阶段的行为起到了预防和打击作用。该罪名来源于普通法系的共谋罪,即只要行为人就不法行为的实施达成合意,便具有可罚性,共谋行为本身即是一种犯罪。为方便大陆法系国家适用,《北京公约》在具体项中分列了两种情形,一是普通法系的共谋或商定犯罪,二是类似大陆法系的团伙犯罪的规定,然后在该款中采用了“两者之一或两者”的写法,缔约国可以根据本国立法,选择适用于本国的普通法系的共谋罪或者大陆法系的团伙犯罪。
从罪名确定上,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在犯罪的预备阶段予以制止;从立法技术上,共谋或商定犯罪条款本身就是国际航空法学界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未来的更新,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国际法上的融合规范,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3. 妥善处理航空保安公约之间的关系
作为对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修订,《北京公约》并非从一开始就有了“公约”之名。在国际民航组织专家研究组、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法律委员会研讨之际乃至北京外交大会召开期间,这部新的国际法律文书的形式仍然没有确定。起草前期阶段,各国重点讨论的是实体内容,包括如何确定罪名、如何扩展管辖权、如何从其他反恐公约中吸收有益规定等;起草后期阶段,各国开展文本形式讨论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将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条款和新增条款合并,形成一部新的公约;二是仅规定新条款,形成一部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议定书。
相较而言,观点二的优点是不用花费较多精力研磨条款,立法技术较为简单,而且可以保留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独立性与存在性。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已经有一部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对其进行了修订,如果未来想系统了解这方面的国际法律规定,需要分别研究一部公约、两部议定书,而且这三部法律文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会存在问题。
在北京外交大会上,经过多方沟通协调,尤其作为此次会议主办国的中国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首先,综合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和新条款,形成一部新的公约;其次,在新公约中明确规定新公约与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的关系;最后,明确三部法律文书批准情形不同,适用情况也各不相同。
简单来说,《北京公约》修订了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作为一部新公约,优先于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和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这种方式既保持了现有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稳定性,原有公约均未失效,又明确了这三部法律文书之间的关系,也便利了各方对该法律体系的研究,对于未来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再次修订,具有示范作用。
三、 《北京公约》获批对中国民航发展意义重大
(一) 展现大国担当
自2005年起,中国民航运输规模已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国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 293.3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6.6亿人次,货邮周转量263.2亿吨公里;定期航班国内通航城市234个(不含香港、澳门、台湾),通航国际65个国家的167个城市[13]。也正是在2019年,中国民航主管部门正式启动了《北京公约》的国内批准程序。
2010年的北京外交大会上,中国作为主办国积极协调斡旋,为以公约形式形成最终文书作出了大量努力。《北京公约》开放签署首日,中国即进行了签署。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民航公约,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场签署公约,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航空合作的意愿,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一贯立场。从签署到批准,表明了中国对于严惩针对民航业的国际犯罪活动、维护航空运输安全的坚定决心和积极态度。
2022年10月,国际民航组织第41届大会上,中国专门提交了《推动批准国际民航法律文书》工作文件,介绍了包括《北京公约》在内的国际航空法律文书的生效情况和中国批准情况,以推动各国批准相关公约,更好实现《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目的、宗旨和原则,保障国际民航活动健康、有序、高效发展。
(二) 保障行业发展
对于航空运输,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面临着严重威胁。国际民航领域,2020年发生非法干扰行为12起,其中炸机和炸机未遂行为2起,劫机行为1起,攻击航行设施行为3起。2021年,发生非法干扰行为42起,其中炸机和炸机未遂行为4起,劫机行为9起,攻击航行设施行为9起。国内民航业以针对民航的虚假恐怖信息威胁为主,仅2022年4—7月,就发生了22起针对民航航班、民用机场的爆炸物信息威胁案件,均为虚假信息。此外,2012年6月29日的劫机事件更是一起典型的恐怖分子企图劫持航空器后造成机毁人亡的犯罪行为。
包括《北京公约》在内的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对上述行为均予以定罪;根据已批准的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结合中国国内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明确定罪量刑,有力保障了航空业的发展。
《北京公约》将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对航空运输业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干扰行为规定为犯罪,规定了广泛的管辖权,吸收了其他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更新和推进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北京公约》获批后,能够进一步保障民航业安全、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保护航空运输企业的合法利益,保障旅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 互通国内国际立法
国际刑法公约并没有规定犯罪的具体刑罚尺度,中国需要适用本国刑法对国际犯罪进行审批和处罚[14]。《北京公约》也是如此,其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与《刑法》有效衔接,主要对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组织罪,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等罪名以及共犯等相关规定。在管辖权方面,《刑法》第6条属地管辖权、第7条属人管辖权、第8条保护管辖权等规定,可以保证《北京公约》规定的相关管辖权在《刑法》中落地实施。
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引入了相关概念,严密了犯罪体系,完善了刑罚配置,尤其是强化了法益保护前置的理念,将一些预备犯、帮助犯分离出来单独定罪的方式,与《北京公约》起草中的理念和条款十分相似。201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怖主义法》)是首部全面系统地规定反恐怖工作的机制体制责任和反恐怖手段措施的基本法,为依法打击恐怖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与保障。其中,专门规定要严密防范针对航空器或者利用飞行活动实施的恐怖活动。
《北京公约》《刑法》《反恐怖主义法》三者合力,能够有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结合国内外反恐实践,共同助力反恐工作。这也是加强反恐法治建设,树立依法反恐思想,确立法治反恐的重要手段。除《刑法》及其修正案、《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外,中国民航安全保卫立法层面也在积极学习借鉴《北京公约》立法中体现的前瞻性、预见性以及对新风险、新威胁的应对措施,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以及民航安全保卫规章的修订,实现“防患于未然”的目标,不断增强防范制止非法干扰行为的能力和水平。
四、 结语
除达成《北京公约》外,北京外交大会的另一个成果是制定了《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2010年《北京议定书》”),该议定书主要修订了1970年《海牙公约》,补充了有关劫机犯罪的内容;4年之后的蒙特利尔外交大会,通过了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主要修订了1963年《东京公约》,补充了违规旅客相关内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在21世纪的前15年,再次焕发活力,实现了更新,无论新的犯罪或违法行为,还是更广泛的管辖权,都纳入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这必将更加系统和全面地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国际民航组织此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各成员国批准上述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并作为近期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和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中国在批准《北京公约》的同时,2010年《北京议定书》的国内批准工作也在按程序推进,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批准研究工作也已经启动。笔者全程参与了《北京公约》制定工作并在此后跟进国内批准相关工作,也参与了2010年《北京议定书》和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制定。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对犯罪分子布下的“天罗地网”必将能在国内全面铺开,从而有效保护航空运输安全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注释:
①参见:Report on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on the Preparation of One or More Instruments Addressing New and Emerging Threats, C-WP/13111, 14/5/08。②参见:《法律委员会第34届会议报告》(中文版),Doc 9926-LC/194。 -
[1] ADUA M I,ABDUL-HAMID O Y.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in the realm of aviation security:The 2010 Beijing Convention in focus [J].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ecurity,2018,11:53—63. doi: 10.1007/s12198-018-0189-x
[2] HUANG J F. Aviation safety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ICAO’s mechanisms and practices [M]. Alphen aan den Rijn Frederic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123.
[3] MILDE M. International air law and ICAO (essential air and space law)[M]. Hague: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8: 229.
[4] 赵维田. 论三个反劫机公约[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5. [5] 张君周.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的非法干扰行为研究[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 35. [6] 李寿平. 论21世纪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面临的挑战与新发展−从马航370事件说起[J]. 法学评论,2014,32(4):145—154. [7] 张卫华. 对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若干修改意见−以国际民用航空安保条约为视角[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0(1):46—53. [8] 黄解放, 刘贺. 《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浅析[M]//中国国际法学会. 中国国际法年刊2010.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9] 张君周. 《北京公约》中“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分析[J]. 法学杂志,2012,31(11):159. [10] 高铭暄, 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 林俊辉. 中国刑法语境中的“共谋罪”考辨[J]. 北方法学,2009,3(2):85—93. doi: 10.13893/j.cnki.bffx.2009.02.014 [12] 杨惠,张莉琼.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新发展−以《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为视角[J]. 中国民用航空,2012,25(8):28. [13]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19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0−06−05)[2022−11−10]. [14] 马呈元. 国际刑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53.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93
- HTML全文浏览量: 251
- PDF下载量: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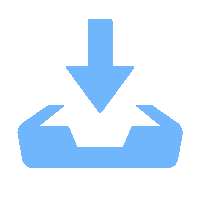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