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for China’s Nature Reserves
-
摘要:
回顾过去60多年的历程,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经历了类型化发展和体系化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中国式自主创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的类型,以及受国际公约和保护计划影响的湿地公园、地质公园、自然遗产地等类型。每个类别的保护地都形成了独立的法制体系,发挥着卓有成效的法治作用。但类别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在管理体制、制度建设和法体系方面仍存在不足,为此,中国进行了两次国家综合立法的努力。在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涵,应当合理选择自然保护地国家综合立法体例,抓住制定《国家公园法》这一契机,实现自然保护地治理向体系化发展转型并促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法治化。
Abstract:Over the past 60 years, China’s nature reserve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the phases of categorized development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forming the types of nature reserves, scenic spots and forest parks with Chinese innovation, and wetland parks, geo-parks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that follo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conservation plans. Each category of nature reserves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legal system which plays an effective role in the rule of law.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categorized nature reserve system. To this end, China has conducted two attempts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legislation. In the new era tha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nature reserves has become the co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legislation style of nature reserves in a rational way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enact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Law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reserve governance to systemat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e reserve system.
-
从1956年中国成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到2019年3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要求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1],再到2022年自然资源部通过《国家公园法(建议稿草案)》[2],中国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在国家公园立法深入开展,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体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的当下,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因此,回顾、总结中国自然保护地法治发展的光辉历史进程和伟大制度成就,展望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的未来方向,对推进中国生态环境法治的健康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自然保护地的术语流变和类型化发展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一般采取划定明确的地理边界,并通过法律、政策、承诺或协议等方式来实施自然保护制度,通称为“特殊环境资源自然保护”,其实际上指向的是特定类型区域的自然保护制度,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①。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地”术语传入中国后,早期变通为“保护区”,后来为区别于中国已有的自然保护区,便使用了“自然保护地”和“自然保护区域”等名称。2003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设立了“保护地课题组”;2004年至今,全国人大曾尝试制定《自然保护区法》,先后推出了《自然保护区法》(草案)、《自然保护区域法》(草案)、《自然保护地法》(草案)[4],为形成自然保护地国家综合立法作出了努力。
中国自然保护地综合立法进程,从外因上来说,是受到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管理体系成熟发展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国际自然保护领域保护地术语泛滥,保护地分类体系凌乱且无统一的分类标准和体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用了25年的时间开发了逻辑统一的保护地分类体系,并形成了统一的保护地术语、分类体系和管理指南,在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和普遍规范意义。但是,当时反映综合管理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管理体系尚未被中国自然保护主流话语体系所接受,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正处于类型化管理的成熟期。
2012年之后,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建设成为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改革的目标是变革部门分立、分类无序的类型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新型的体系。此时,1994年版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分类体系和管理指南已经发展为国际广泛适用的“共同语言”,也逐渐为中国自然保护主流所认可,并成为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顶层设计的重要参考。所不同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地”术语在中国正式规范语境中变为“自然保护地”,此术语流变首先考虑与中国业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相区别,其次考虑保护地客体对象的原真天然性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单一类型自然保护区创建发展阶段,自1956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创建形成中国自然保护区体系。二是类型化自然保护地创建发展阶段,自1982年第一个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建立至2013年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地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陆续加入许多重要的自然保护国际公约和国际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自然保护地数量和面积的快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制度建设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自然保护地类型从一个发展至十多个,顺次为:风景名胜区(1982年)、森林公园(1982年)、世界遗产(1987年)、地质公园(2001年)、水利风景区(2001年)、湿地公园(2005年)、城市湿地公园(2005年)、海洋特别保护区(2011年)、海洋公园(2011年)等,覆盖了中国主要的自然保护空间客体[5]。然而,中国自然保护地实存体系虽看似类型丰富,但因自然保护地发展以类型扁平化结构展开并未遵循逻辑一致的分类体系,因此,所形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缺乏真正的体系化意义,还只是自然保护地的集合[6]。三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综合性建设阶段,自201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展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其中,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既是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以中国实践、中国国情为基础。无论是构建自然保护地新的类型体系,还是开展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建章立法工作,都需要考察规范语义下的自然保护地实存体系及其法治现状,并以此来谋划改革策略、建设应然图景。因此,考察中国类型化自然保护地创建发展阶段(上述第二阶段)所形成的六类较为成熟的自然保护地类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自然遗产地的发展状况、法律法规体系构成及其实施成效等法治状况,能够为未来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综合立法、国家公园立法提供经验和现实条件。
中国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发展阶段,主要形成了中国式自主创新的和受国际公约影响的两大类别的自然保护地。
(一) 中国式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两区一园”
中国自然保护地的“两区一园”,是指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是“自主创新”的中国式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两区一园”占中国自然保护地面积的大部分,也是保护地交叉、重叠设置最多的类型。在类型化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就保护目标而言,自然保护区采取最严格的自然保护,其保护目标具有唯一性;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则是保护对旅游和游憩兼顾的保护类型,但其自然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
1.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是指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等为目的,通过行政程序划定一定范围的自然区域,在区域内采取限制或禁止人为活动的方式,避免或减少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的破坏和影响。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最早发展形成的自然保护地类型。早期的自然保护区约等于天然禁伐区,主要建立在天然林区且数量较少,还常常遭到破坏或撤销。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1978年作出关于加强武夷山生物资源保护的重要批示,促成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设立。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重新颁布,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也相继出台,中国自然保护区开始步入法制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向系统性保护转变,一个数量充分、类型齐全、功能完整、布局合理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已经基本形成②。随着2015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的实施,自然保护区数量的增长进一步放缓。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有着显著特征:一是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客体的自然性最强。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和保存指定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和过程、生物物种或自然遗迹为主要目标,因此,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客体形态具有代表性、稀有性和多样性的特殊价值。二是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方式最严格。自然保护区采取封闭式保存的方式对自然区域进行保护,人为干扰仅限于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提倡人为的“建设性”的保护措施,不为旅游观光所利用,不以经济性增量为效益目标。三是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体系发展得最完整。中国形成了在《宪法》和《环境保护法》规范统领下,由“国家法律—专门行政法规(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构成的形式较完整的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体系。其中,有十多部国家法律关涉自然保护区保护③。
国务院1994年颁布、2011年修改的《自然保护区条例》是中国首部,也是现行最重要的一部统一规范各类型自然保护区的行政法规④。一系列的部门规章,重要的政策性文件⑤和地方性法规在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设立了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大部分还进行了管护站点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经费,中央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适当财政补助。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形成了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等生态保护国际公约的国内实施机制,并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广泛的自然保护区国际合作。
2019年发布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提出的新型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中,不仅保留了自然保护区的类型,并赋予其在体系中处于“基础性类别”的重要地位,支撑新兴的“主体性类别”国家公园的创建和发展,许多国家公园即是由既有自然保护区优化整合而成。
2.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是指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首先,风景名胜区具有风景名胜资源禀赋。中国风景名胜区源于中国古代的名山大川,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其自然基础是动物、植物、山脉、水系、农田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它不仅是一个环境要素、自然景观,同时还是一个承载着哲理、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中国文化的自然体,是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融合的自然文化综合体,具有重要的文化欣赏、传承和弘扬的功能。其次,风景名胜区具备便捷的游览条件。因此,从保护目标上来看,与自然保护区仅具有自然保护这一唯一的目标不同,风景名胜区具有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欣赏并重的双重目标。
1982年,中国正式开始建设风景名胜区制度,几乎同时开展法规建设工作。经过40余年的发展,风景名胜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由申报、规划、保护、建设、监管督察等环节组成的较为成熟的管理制度。中国成为近30年来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⑥。
相较于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中国风景名胜区的法制建设有着最坚实的宪法和法律基础:《宪法》强调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第22条),《环境保护法》把风景名胜区列为环境的一个组成要素予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保护自然景观,加强城市园林、绿地和风景名胜区的建设。目前,中国风景名胜区保护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以下简称《风景名胜区条例》),以及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部门规章和技术规范⑦。地方性立法成为风景名胜区保护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现行行政法规《风景名胜区条例》,是在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和1987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暂行”实施20多年后,于2006年正式颁布实施,并于2016年修订。2016年的修订着重解决保护规划编制不规范,审批制度不完善,规划法律地位低,保护、利用和管理措施不足,管理机构的设置、性质、职能不规范,以及景区经营和门票收入管理混乱等问题。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以《风景名胜区条例》为主体的风景名胜区法规体系已经相对完善,为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制基础。
然而,在2019年《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提出的新型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中,无论是在自然保护地的大类(指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还是自然公园的子类(列举式表述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海洋公园等”),风景名胜区类别都不在其列。而在环境法体系中,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区是传统类型化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类型,是体系中的两大支柱。因此,风景名胜区在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地位和定位问题仍然是未来自然保护地体系法治建设需要完善的重要内容。
3. 森林公园
自1980年起,原林业部开始建设森林公园、发展森林旅游,同年发布《关于风景名胜地区国营林场山林和开发旅游事业的通知》,进行森林旅游工作部署。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81年首先提出兴建森林公园。在进行了中央和地方合资兴办、科学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森林公园试点后,上述两部委在具备条件的国营林场组织兴建森林公园,1982年成立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20世纪90年代,国有林场管理权开始从省级或市级政府下放至县级政府,实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的改革,国有林场为了克服贫困开始发展森林旅游,产生了显著的旅游经济效益。自1994年以后,国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成为森林产业转型的新型业态。2002年后,中国林业开始发生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根本性转变,森林公园成为兼具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推动林区经济增长双重功能的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经过40多年的努力,兼具森林保护与生态旅游功能的森林公园在中国自然保护事业中开始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比肩的三大自然保护地类型之一。
有关森林公园保护和管理的国家法律主要是《森林法》(2019年),该法没有直接规定森林公园的条款,但是该法第31条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原则规定涵盖了对森林公园的保护,即“国家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林生态地区、珍贵动物和植物生长繁殖的林区、天然热带雨林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天然林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保护管理”。目前,中国尚无关于森林公园的专门行政法规,开展森林公园保护与管理的主要依据是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一系列操作性较强的行政规章,主要是《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级森林公园监督检查办法》《国家森林公园设计规范》《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审批管理办法》等。这些规章对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内部设施建设、活动开展、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规定。目前,还制定了数量较多的关于森林公园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森林公园是中国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之后发展最迅速、制度建设最全面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从管理体制方面来分析,这是林业部门单独管理和推进的保护地类型,具有行政便捷、有效的优势;从经济发展方面来分析,森林公园建设是带动国有林场产业转型、发展林业生态旅游的新业态,由于成本和收益显著而获得有关部委以及社会资本的较大投入;从法制保障方面来分析,主导森林公园保护管理的规范依据是国务院部门规章,立法位阶较低,森林公园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森林公园的使命和公益性质等问题还需要具有更高层级的立法来予以明确和维护。
尽管如此,森林公园保护和管理的法制建设在很多方面仍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其一,形成了“森林公园”的正式定义。1982年,国务院在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开始研究森林公园的概念和科学内涵。“森林公园是以森林自然环境为依托,具有优美的环境和科学教育、游览休息价值的地域,经科学保护和适度建设,为人们提供旅游、观光、休息和科学文化活动的特定场所”[7],这是国内学者首次正式提出的关于森林公园的定义。《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森林公园,是指森林景观优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物集中,具有一定规模,可供人们游览、休息、或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该定义与从自然科学角度制定的国家标准(GB/T 18005—1999)中所述的森林公园,即“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森林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森林旅游,并按法定程序申报批准的森林地域”,共同构成了森林公园的规范语义。诚然,该定义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解释了森林公园的自然科学意义和客观功能内涵,但忽视了其社会属性,尤其在公益与私益、开发与保护的制度功能上的价值判断。其二,整章建制,规范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国家林业主管部门自1992年起开始着手森林公园建章立制工作。森林公园的法律法规体系,并没有像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保护一样存在一个操作性强并具有正式上位法位阶的国务院行政法规,而是以部门规章为依据开展森林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在2015年以后,原国家林业局显著加强了对国家级森林公园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建立了国家级森林公园名录、执法人员名录库和专家名录库,开展森林公园自然教育培训,设立森林公园解说员制度,深入推进森林公园的规范化管理。这是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一个行动响应。其三,重视处理保护地规划交叉重合问题。自然保护地建设中,保护地交叉重合规划是形成“一地多牌”的主要原因。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也存在如何处理保护地交叉和重合规划的问题。《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对此冲突进行了协调,其第9条规定,已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范围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有重合或者交叉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间应相互协调;对重合或者交叉的区域,应当按照自然保护区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这一规定符合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立法原则。针对同样的问题,省级地方性法规亦开始重视,但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避而不谈,如《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二是实施统一经营管理,如《陕西省森林公园条例》(2012年)规定“森林公园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重合或者交叉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整合管理组织,实施统一经营管理”,这一规定放权于地方人民政府,笼统要求整合管理。三是采取交叉管理和统一管理,如《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5年修正)。四是建立执法监督机制。林业主管部门的执法监督主要是以“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为依据,加强对规划审批和规划实施的执法监督和检查。自2016年始,原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对未编制总体规划或总体规划到期不修编的53处国家级森林公园,责令18个月内完成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编制和上报工作。对于逾期仍未上报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致使无法发挥国家级森林公园的主体功能的森林公园,将依照《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予以撤销⑧。
2019年《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提出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森林公园位列自然公园类别的子类,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国际自然保护计划促进形成的自然保护地类型
在中国类型化自然保护地建设中,有一些类型是因中国加入国际自然保护公约、实施相应的国际自然保护计划而促进形成的。这些自然保护地类型主要有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自然遗产地。前两类自然保护地成为2019年形成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中自然公园大类中的子项类别,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湿地公园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开展保护自然湿地并恢复退化的湿地生态系统,1972年签署了《湿地公约》,中国于1992年加入该公约。为了履行国家义务、有效保护湿地,200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4〕50号),提出“要把湿地保护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作为重要工作纳入责任范围,从法规制度、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管理体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该通知成为湿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政策指导和依据,也最早区别了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湿地公园的关系:对生态地位重要或受到严重破坏的自然湿地,要划定湿地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有效的保护;对设立自然保护区还不具备条件的,要“采取建立湿地保护小区、各种类型湿地公园、湿地多用途管理区或划定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等多种形式加强保护管理”。按照湿地的重要性程度,将湿地划为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湿地公园、湿地小区等保护区域。这也成为了中国湿地保护政策与法律文件遵循的基本思路。
2005年2月,原建设部(已撤销)印发《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界定了城市湿地公园范围、申请条件。之后,中国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国家湿地公园相关配套的规章与技术规范,如《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验收办法(试行)》。2006年通过的《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2005—2010年)》(即湿地保护“十一五”规划)对湿地公园进行了界定:“湿地公园是指湿地景观自然典型,风景资源优美,具备相当的旅游休闲设施,可供人们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并能进行科普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建立湿地公园的目的是要保护湿地生态功能的完整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湿地公园是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一种新型的湿地多用途管理区,是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一种新方式。”2010年通过的《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首次系统性规定了国家湿地公园的定位、监管机构以及建设基本原则和条件等。
2013年通过的《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明确了湿地公园的基本类别,即“湿地公园分为国家湿地公园和地方湿地公园”。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细化了湿地保护的区域类型,要求“对国家和地方重要湿地,要通过设立国家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等方式加强保护,在生态敏感和脆弱地区加快保护管理体系建设”。同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定:“在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逐步恢复湿地生态功能,扩大湿地面积。”此时,中国以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湿地公园和湿地小区并存及其他保护形式互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初步建立。
202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通过并于2022年6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2条规定:“湿地是指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者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外。国家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该法第14条规定:“国家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按照生态区位、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级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般湿地。重要湿地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该法还对天然湿地、人工湿地、城市湿地的保护措施进行了规定,但未明确规定“湿地公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关于编制湿地保护规划的要求,2022年11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
2022年11月,中国首次承办《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并担任此后三年大会主席国和公约常委会主席国,推进公约国际合作。《湿地公约》秘书处将向中国13个城市颁发湿地保护在生态保护领域的最高荣誉“国际湿地城市证书”,至此,中国城市湿地公园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 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是以地质遗迹和重要古生物遗址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类型。目前,地质公园按照地质遗迹景观资源的科学价值、管理等级分为四级管理,即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省级地质公园和地方级地质公园,分别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土资源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及市(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命名。国家地质公园,是指以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优雅的美学观赏价值,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分布范围,并具有全国性代表意义的地质遗迹为主体,并且融合其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而构成的特定地区。国家地质公园以保护地质遗迹、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为人们提供具有较高科学品位的游览观光、科普教育、科学研究、休闲度假、康疗保健的场所。
综观中国地质公园的发展,主要呈现两个发展特点:
第一个发展特点是,地质公园保护地类型最早是以地质自然保护区的形式开展,从诞生伊始就与自然保护区重名建设。1985年,原地质矿产部在长沙召开“首届地质自然保护区区划和科学考察工作会议”,在与会代表倡议下,于当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武陵源国家地质公园”。1987年,原地质矿产部发布《关于建立地质自然保护区规定的通知(试行)》,全国开始建设融保护珍贵地学自然历史遗产与旅游、科研、教育等目的为一体的地质自然保护区,陆续建成多个国家级、省级和县级的地质自然保护区。1995年,原地质矿产部发布《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规定了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保护地形式是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和管理的总体要求以及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建立程序。
第二个发展特点是,地质公园在1995年后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国际地质遗迹保护进程的影响。国际地质遗迹保护的正式制度安排,可溯源于《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1972年)的履约计划。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华盛顿启动了“全球地质及古生物遗址名录的国际地质对比计划”。该计划在1997年发展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促使各地具有特殊地质现象的景点形成全球性网络计划”(即“地质景点计划”)。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了“具有独特地质特征的地质遗址全球网络”,同时诞生了“地质公园”(geopark)这一新名称,提出建立500个世界地质公园的全球计划,中国成为试点国家。1999年,原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工作会议”,提出在开发和保护协调统一框架下建立国家地质公园。2001年,中国首批11个国家地质公园审批成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建立了世界地质公园网络(Global Geoparks Network,GGN),办公室设在中国。2004年,第一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在北京召开。
为了规范建设,原国土资源部于2005—2008年期间暂停了国家地质公园的申报,在2009年重启第五批申报后常规化地每两年审批一次。国家地质公园审批程序也做了修改,国家层面只授予国家地质公园资格,申报单位需按地质公园建设标准建设,经由国土资源部验收合格后才能正式批准、获得国家地质公园称号。
中国陆续颁布实施了一些国家法律,对地质遗迹的法律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对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等自然遗迹,以及人文遗迹、古树名木,应当采取保护措施,严禁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中必须包含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也有相应地质遗迹的保护规定。
目前,国务院尚未颁布地质公园保护的专门行政法规,与地质遗迹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主要有《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地质公园建设、管理和保护的直接规范依据主要是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由原国土资源部等部委颁布的部门规章和技术规范⑨,以及与世界地质公园有关的国际软法规范(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工作指南》)。这些规范涉及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资格授予和批准命名分开审核的制度、地质公园规划、地质遗迹保护、解说系统建设、科学研究和科普、管理和信息化、批准命名、实地评估检查等。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家地质公园纳入国家禁止开发区域,并要求依据该规划确定的原则以及《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工作指南》和地质公园规划开展管理。管理和保护措施包括:在国家地质公园以及对地质公园可能造成影响的周边地区,除了必要的保护设施和附属设施外,禁止进行其他的生产建设活动;禁止采石、开矿、取土、砍伐、放牧等对保护对象产生损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地质公园的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可见,地质公园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成为极具国际标准管理特色、与国际自然保护接轨,甚至引领国际地质公园计划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类型,彰显了中国地质公园法治建设的积极成效。借鉴国际保护经验形成的国家地质公园管理督察员制度,更是成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保护和管理中的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监督管理制度⑩。
当然,地质公园的管理和保护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地质遗迹直接依据国务院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且规章对地质遗迹保护类型及级别界定较为模糊。例如,《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工作指南》(2000年)是最早出现的地质公园按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的重要程度划分行政级别(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的分类管理原则。其中,国家级地质公园的标准强调了自然科学的价值,但缺乏对社会价值的考虑。其二,对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协调不够。对地质遗迹的认识不足,在管理理念上不能始终将地质遗迹的保护放在首位,在旅游经营管理上回避或弱化科普展示教育功能,较少开展地学意义上的解释说明,多采取的是与一般风景名胜区类似的经验管理方式等。一些地质公园甚至出现过度利用现象,如营建人工设施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等问题[8]。其三,地质遗迹保护分区的科学性有待加强。较多地质公园遗迹保护规划忽视了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以点、线、面交互存在的实际情况,而照搬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及实验区三圈保护模式,致使地质遗迹的保护成效甚微[9]。其四,与其他规划衔接不足。地质公园保护规划与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旅游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的衔接性与整合性较差。各类保护地边界与其他规划边界模糊,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保护与潜在的矿产、水等资源开发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其五,地质遗迹保护管理体制不顺,存在多头管理、跨行政区域管理等问题。
3. 自然遗产地
自然遗产地,顾名思义是保护自然遗产的特殊区域,在管理实践上已然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类型。然而,笔者从国内法规范语义分析的角度来判定,却发现其有名不副实之嫌。
“自然遗产”或“自然遗产地”并非中国自主发展起来的自然保护地概念,而是来自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法。世界遗产保护国际法发展,可溯源于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二届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十年之后,联合国通过了自然遗产保护的专项国际条约−《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该公约及其缔约国通过的决议,加上履约辅助性技术规范共同构成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体系。《世界遗产公约》明确了需保护的自然遗产及其认定标准、遗产保护的国家责任,缔约国大会成立、设立“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基金”来开展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2016年《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是由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最重要的国际技术规范,对《世界遗产公约》中一些过于简化的条款进行了细化。该指南内容详尽,可供各缔约国参考操作。例如,该指南第63条规定,一般情况下一项世界遗产的申报,进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前置程序;第178条规定,名录的变动代表着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权威决定,世界遗产被列入或被移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不以缔约国提出申请为条件,世界遗产委员会可根据监测、评估结果自行决定。
《世界遗产公约》第2条以列举形式定义“自然遗产”,这是一个宽泛的、以描绘自然和科学属性为主的自然遗产定义。第3条规定,缔约国均可自行确定和划分上面第1条和第2条中提及的、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进一步提出划分自然遗产的细化标准。可见,《世界遗产公约》鼓励各缔约国在其国内法中对“自然遗产”进行实质化拓展。如果说中国地质公园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质遗迹国际保护进程的影响下发展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规范语义和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同样受国际自然保护进程影响的中国自然遗产地,在国家履行《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自然遗产保护的进程中则并没有形成关于“自然遗产”和“自然遗产地”的本土化的国家层面的规范概念,也没有形成国家层面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和保护制度体系。“国家自然遗产地”是中国自然遗产保护较为正式的术语和主要客体,但其与“自然遗产”“自然遗产地”一样,国内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均未进行直接规定,也无专门定义和解释。2007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对“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提出了一个规范性定义⑪,是指“在科学研究、自然多样性保护、历史、艺术和审美角度具有国家意义的自然或文化和自然混合型保护地”;在外延上,包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村、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无论是国家自然遗产还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遗产”是一个兼具保护与利用的国际自然保护标签,具有绿色品牌效应和人文、社会等附加价值,对带动自然保护地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最早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目前,中国在世界遗产名录国家中排在第一位⑫。中国许多著名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都享有世界遗产称号。
为了专门规范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的管理工作,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了《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内容涉及总则、申报、保护和管理。从该办法第7条所规定的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基本条件可推断分析,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地”的外延包括:列入《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自然保护地单位;依法划定的省级及以上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地。该办法规范了中国世界遗产预审程序和世界遗产跨行政区域的协调管理机制。
笔者认为,自然遗产地虽然已经成为中国实存性的自然保护地,但从国内法渊源上来看,它还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和完整规范语义的自然保护地。与同样具有国际化性质的地质公园保护地的法制建设不同,中国自然遗产保护地的法制建设,在国家层面既未形成自然遗产、世界遗产的国内法规范语义,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综合的自然遗产管理机构,也未能出台一部正式的、专门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因而也就没能形成完善的规范体系。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实际管理往往依赖于其他已有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最常见的便是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制度。
地方立法是中国自然遗产保护地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法治意义更在于对普遍意义上的自然遗产所开展的有益的制度探索和对一定程度上的法律渊源的填补。据笔者考察,中国自然遗产保护地方性立法存在三种模式:一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之“世界遗产”而非针对“专项世界遗产”的立法,如《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2015年)⑬;二是针对符合普遍意义上的特定的“自然遗产”而非“世界自然遗产”的立法,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2011年);三是针对申获成功的特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一地一法”式的专属立法,多数地方性法规属于此种模式⑭。
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前,中国自然遗产管理还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这或许是自然遗产地法制建设不完善、未形成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自然遗产保护和管理法规体系的体制根源。自然遗产保护中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十分紧张,政府财政拨款极其有限,自然遗产的门票和旅游收入往往收归遗产保护管理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管理部门即使是旅游收入增多,保护资金也仍然匮乏,保护管理部门与经营实体企业往往政企不分,世界自然遗产即使极具公益性质也还是抵挡不住过度私有化、市场化,或是私利驱动带来的不理性获利和分配。一些自然遗产地包装上市,获得的利润成为企业经营收益的一部分,反哺保护严重不足[10]。
2018年3月,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为自然遗产地法制建设带来了新机遇,自然遗产地的管理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等整合,由新组建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归属自然资源部管理。
二、 中国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发展的法治困顿
中国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发展历经60多年,从无到有,形成了自然保护地类型化体系及各类型法制框架,奠定了中国自然保护地较为坚实的法治基础,成为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所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发展存在着体制、体系和立法方面的问题,因此也导致了自然保护地法治运行上的困顿。
(一) 管理体制不顺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前,自然保护地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和政府多部门管理体制体系,存在统筹管理的部门缺失,管理层次多、部门重叠、职责不清晰,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不合理、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问题。自然保护地因提供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属于国家生态安全事务,理论上,应当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法规要求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资金根据其所属的不同级别和隶属的不同部门,分别由国家、地方或者部门负担。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的自然保护地,地方政府均为主要的负担者。由于地方政府负担区域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等职责,往往采取短视的方式来对待自然保护[11],将自然保护地作为产生经济效益的资源(如违法在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经营),忽视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的管理原则,偏离了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目标[12]。
应该看到,在“十五”规划之后,自然保护地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资金(主要以项目形式)的比例逐渐增大,在个别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中甚至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13]。这种财政投入安排有必要上升为法律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财政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承担责任。
(二) 类型化管理混乱
实践中,自然保护地规划区域交叉重叠、一地多牌、重复命名的情况较为普遍,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这种情况在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之间、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之间尤其突出[14]。保护地重复命名问题意味着保护地管理机构林立、部门主管增多,建设和管理的依据也不统一,综合管理或统一管理难以为继。类型化管理混乱直接影响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的执法地位和能力。通常,自然保护地由政府相关部门设立管理机构,然而,其究竟属于政府派出机构还是独立法人、是否具有执法权力,都未予以明确[15]。
国务院已经充分认识到一地多牌和交叉管理问题,并在行政立法上予以了响应,但是尚未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在1985年《风景名胜区暂行条例》实行21年后的2006年,国务院制定了《风景名胜区条例》,就自然保护区重叠规划和交叉管理问题首次提出了解决方案。在空间规划上,新设立的风景名胜区不得与自然保护区重叠交叉,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应在规划上相互协调(第7条第2款);在管理上,“风景名胜区内涉及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文物保护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还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第34条第2款)。但是,这些规定都是针对新设立的风景名胜区的,对已经设立的风景名胜区且存在与自然保护区重叠规划和交叉管理问题的,仍然未能予以解决。2011年国务院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对自然保护区与其他保护地的关系问题,包括与风景名胜区存在的重叠规划和交叉管理问题,并无相应规定,对历史性的重叠规划和交叉管理问题也没有进行协调和厘清。
(三) 法体系疏漏
类型化发展主导下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和法规体系建设存在较大缺陷。
首先,缺乏统领性的综合法律。有关自然保护地宪法、法律层面的规范依据,只能转致于“自然保护地”最接近的条款。2018年修订的《宪法》第26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是整个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的宪法依据,当然也适用于“自然保护地”保护。《宪法》第22条“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规定,为与名胜古迹、文化遗产直接关联或关联紧密的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比自然保护区享有更高的宪法和法律地位。《环境保护法》(2014年)第29条关于生态红线制度的法律规定,是目前能够涵摄所有类型自然保护地且最接近“自然保护地”统一术语的基本法律规范。应当注意的是,此条规定实际指涉“自然保护区域”,其保护自然客体外延指向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生物多样性区域、水源涵养区域、自然遗迹(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川、火山、温泉等)、人文遗迹、古树名木等;而这些非直接调整的法律条款对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显然不够充分。
其次,立法层级不高、法规结构不合理。中国自然保护地发挥效力的法律规范渊源主要是行政法规和规章,《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是行政法规,《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地质遗迹保护管理办法》是国务院部门规章。这种缺乏自然保护地综合法,主要规范依据是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的状况,反映出立法上自然保护地法律规范结构不合理,法律规范在实施中也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不能解决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问题[16],以及保护地管理上的重叠规划和交叉管理等问题[17],同时也增加了执法难度,不利于实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目标。
最后,立法更新不及时、立法内容滞后。中国自然保护地的主要法规和管理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服务于经济增长、忽视环境资源保护是上述发展时期的时代局限。即便是在先进的国际环境保护潮流引领下,自然保护地保护和建设如世界遗产申报也不可避免地会被经济增长势头裹挟和冲击,许多保护客体非但达不到保护效果反而遭到人为破坏。以风景名胜区为例,风景名胜区法规体系立法更新滞后,其暂行条例试行20多年后才颁布正式条例,在内容上也往往重开发利用而轻保护。
三、 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发展进程中国家综合立法的努力
鉴于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发展遭遇的体制瓶颈和法治困境,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2012年开展了自然保护地国家综合立法的积极探索,经历了《自然保护地法》和《自然遗产保护法》两个议案的审议阶段⑮。
(一) 第一次国家立法努力:《自然保护地法(草案)》(2006年)
自第九届全国人大以来,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受到重视,主要管理部门和立法机关意图将《自然保护区条例》上升为国家法律来解决自然保护区这一类型保护地的管理体制等诸多问题,故于2004年2月《自然保护区法》被列入第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第二类立法项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环资委”)提出议案。在起草过程中,全国人大环资委就法案的名称、调整范围、分类管理制度等重大问题征求、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主张如果局限于仅将《自然保护区条例》上升为《自然保护区法》将仍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倾向采取“自然保护地法”立法路线,制定综合法整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不同类型的保护地,因为这些保护地都有着保护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障珍贵资源不因过度利用而被破坏的共同目标。2006年2月,全国人大环资委提出了《自然保护地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共6章68条。该草案对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分类管理、资金投入、规划、评审和评估机制、公众参与和社区共管、土地权属和生态保护补偿作出了规定。
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地国家综合立法的第一次极富改革锐意的尝试,其立法目标不再局限于为某一特定类型的保护地进行国家立法,而是为所有类型的保护地进行系统立法,通过立法理顺保护地各类型之间的体系关系和管理体制,解决不同法规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问题。《自然保护地法(草案)》最具创新性也是最受争议的制度有两项:
其一,该草案提出了“统管+分管”的管理体制。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由原有的“综合管理”改变为“统一监督”,对开发利用活动甚至自然保护活动本身进行监督管理,这一定位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对生态环保部的职责规定相吻合。
其二,该草案提出了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衔接的、自主的保护地管理分类标准和体系。立法者已然认识到,中国的自然保护地是以保护对象为分类标准进行的分类。这种分类方法简明、直观,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乏明确的管理目标,导致法律的保护范围不能涵盖对自然保护区以外的其他类型的保护区域。这不仅与保护地管理制度的设置脱节,而且也不同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所以,中国类型化发展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难以建立多元化综合性的科学管理模式。为此,该草案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分类标准为指引,将中国各主要自然保护地类型按照管理目标和要求分为三大类型−Ⅰ类严格保护类、Ⅱ类保护优先并适度利用类、Ⅲ类定向保护并可持续利用类,并以此作为实施分级、分区管理和定义各类管制措施的统一基础。该草案还提出,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首先对其主管的自然保护地按管理类别进行确认或调整,在征求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意见后,由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协调统一,最后由国务院批准。其中,划为Ⅰ类严格保护类的自然保护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和部分省级自然保护地。针对不同的区域,该草案还规定了不同的财政支持力度和管理措施。
但是,《自然保护地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遭到了一些职能部门不同程度的反对。例如,林业部门认为,自然保护区现行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不尽合理,要求将草案的“统一监督”管理体制改为由各资源主管部门主管相应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基层管理部门和官员以及一些学者甚至难以接受“自然保护地”术语。《自然保护地法(草案)》议案最终没有进入第十届全国人大审议程序。
诚然,《自然保护区法》仅就某一类保护地立法显然无法解决横向保护地之间的衔接和协调管理问题,立法机构将之上升为《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2006年《自然保护地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内容具有合理性,却不能前行,反映出中国特殊区域的自然保护在理念上相较于国际相关集体行动存在滞后性,因抱守“自然保护区”的概念和观念,而不能以开放、兼容和协同的方式处理自然保护地综合管理机制问题,只能说,管理实务部门还没有真正准备好迎接并利用自然保护地国家综合立法的宝贵时机。
(二) 第二次国家立法努力:《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2010年)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继续关注自然保护地立法。由于时值全国世界遗产申报热潮,考虑到中国自然遗产保护除了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及其技术规则外,既无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亦无专门的实体法规范,故与自然保护地密切关联的《自然遗产保护法》便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由于这次自然遗产法起草制定过程亦胸怀整合几个重要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立法目的和雄心,故笔者认为,这是一次承续上一届全国人大未竟事业,锐意进行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发展的立法努力,只不过此次自然保护地体系化的整合是以自然遗产地类别为统帅。事实的确如此,全国人大环资委在自然保护地立法工作的基础上展开了自然遗产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2010年4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公布了《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的立法思路是:首先,确立“自然遗产”法律定义、内涵,明确定性标准;其次,在保护对象和客体语义明晰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自然遗产保护的管理体制和基本制度。该草案将“自然遗产”界定为“从科学、审美和保存角度在国内外具有突出价值,自然演化形成的,反映重大生物和地质历史发展过程,需要依照本法规定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栖息地、重要的地质遗迹以及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景观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该草案除了对“自然遗产”的定性界定外,还规定了其外延所指是“自然遗产包括国家批准的国家自然遗产和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世界自然遗产”,而国家自然遗产又指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⑯。该草案提出的自然遗产,在保护范围上排除了以下客体对象:一是没有规定也不包括地方自然遗产。对具有地方代表价值的自然保护地,没有涉及地方自然遗产级别,而将地方自然保护地保护和管理的权限留给地方。立法者解释,这样“更有利于国务院颁布的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实施,更有利于带动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在内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规范健康发展”。二是不包括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立法者解释说,生物物种的保护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来调整,自然遗产保护法侧重对栖息地的保护;本质上,保护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栖息地,就是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保护生物物种,两者是相互衔接的。该草案关于“自然遗产”法律概念的界定,说明《自然遗产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和功能在当时是有创新意义的。该草案的立法意图是设立新的独立的自然遗产保护对象和区域,也即现代的“自然遗产地”类别,它并不撤销其他保护地类别;但是它又有一定的综合和整合其他自然保护地的功能,也即《自然遗产法(草案)》所定义的自然遗产(无论是保护对象还是保护区域)是从已有类别的自然保护地中剥离重组而成的,这种综合、整合的功能已经在目前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实践中彰显淋漓,其制度创新源头或可追溯于此。
《自然遗产法(草案)》以“科学规划、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传承后世”为原则,设计“一般规定”“国家自然遗产的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和管理”“评估和监督”四章内容,重点强化“自然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该草案维持了已经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实行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和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监督管理的体制,明确自然遗产由环保部门综合管理和建设部门主管的管理体制,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监督管理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责任。
《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在2011年、2012年广泛征求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关于“自然遗产”保护对象、名称和保护范围的规定,专家意见不一。据笔者参与立法咨询会议的记录,一些专家认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符合国家层面自然遗产的保护对象的条件,但对“自然遗产”的定义则有两类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自然遗产应当涵盖中国所有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二是认为自然遗产不应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挂钩,而应当由国务院重新认定。而关于管理体制的规定,该草案受到包括林业部门的强烈反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专家也强烈要求放弃自然遗产法制定而回归《自然保护地法》的制定⑰。随着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届满,《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在反对声中偃旗息鼓。
诚然,中国自然遗产保护尚缺国家立法,《自然遗产保护法》若能完成构建中国专门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任务,则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其遭受反对固然有部门利益博弈因素,但笔者认为,其最大的失利还在于对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架构逻辑的不清晰以及由此引发的法技术错误,这使得《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法律保护目标的规范语义构建与法案意欲承载的功能不匹配。可以明察的是,受《自然保护地法(草案)》的影响,《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仍胸怀整合各类型自然保护地、形成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理想。这一理想使该草案的规范语义架构逾越了构建独立类别的自然遗产保护地体系的本分和初心。虽然该草案给出了较符合国际公约的自然遗产定义,但是该草案对自然遗产的外延客体的法律拟制,已经偏离自然遗产特定类型保护地的特征而呈现整合多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功能面向,实质上扭曲了自然遗产应有的规范语义。
实际上,自然遗产规范语义的制定,可以沿循两条不同的逻辑主线:一是作为所有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统合、集成,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保护地类型。无论选择哪条逻辑路线,都应该在术语定性、对象客体和制度规则上构建逻辑一致的规范体系。而就当时立法实践而言,第一条立法逻辑路线的命运已经随着《自然保护地法(草案)》的逝去而凋零,故《自然遗产法》只能采取自然保护地独立类别之立法定位。然反观草案,其似乎在走一条各部门都不看好的折中路线:它在自然遗产的性质定义上机械地引用国际公约的自然遗产的概念,在保护客体上则有意识地选择“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保护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纳入草案保护范围,而将非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仍然停留在其所属的原自然保护地类型。这样一来,自然遗产地就成为了驴马不分的自然保护区域,非但不能厘清拟制的新法与原有《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的关系,而且更易招致各方质疑,林业部门则对此反对更甚。如果说林业部门对此前的《自然保护区法》草案提案是部分反对,那么对《自然遗产法》法案提案则走向了完全反对的立场,全方位反对自然遗产法的立法动议、调整对象、管理体制。为什么仅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些核心区域纳入新法保护的客体范围,而不包括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呢?划离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其原所属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价值和目标还仍然存在吗?在《自然遗产法(草案)》所定义的管理体系中,林业部门既不是综合管理部门也不是主管部门,还在分部门管理权中失去了对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权。因此,《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失利在于立法路线选择的失败,不走独立类型保护地立法路线,缺乏自然遗产的自主性定义和独立的技术评价标准,终致未能构建起内在合理统一的自然遗产保护法体系。
(三) 自然保护地国家综合立法阻却之因分析
2004—2012年,全国人大环资委主导的起草制定《自然保护地法》和《自然遗产保护法》的活动,实则是对规范语义下综合性自然保护地体系所进行的两次国家统一立法尝试,都未能修成正果。自然保护地法案,通过两届全国人大环资委的持续努力和竭力促成纳入了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却止步于法律草案,无缘步入立法审议之门,这种情形在国家环境资源立法工作中并不多见。体系化自然保护地立法进程的受阻,恰恰反映出类型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的体制痼疾。从《自然保护地法》到《自然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讨论过程,均极大地受到部门利益博弈的阻滞,两次自然保护地国家综合立法的时机也就在部门利弊权衡和制衡之中错失。
《自然保护地法(草案)》的内容和社会反响还反映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地分类体系如果生硬地套用和搬用到中国也会出现明显水土不服,因此,还不能完全拿来主义地充当中国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机芯。而且,较多实务部门人士乃至专家学者,对规范语义下的自然保护地概念不认同或缺乏认知,固守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发展,甚至是绝对类型化发展的传统思路;而接受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发展思路的立法者和管理者,则出现了法技术上的逻辑失误甚至错误。《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选择自然遗产作为自然保护地综合性发展的元概念,机械地将现有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制定为自然遗产的主要对象之一。从类型化自然遗产地发展和法制体系形成的脉络上可以看出,自然遗产地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国际既有的法律调整规范体系,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不宜成为体系化发展模式下的自然保护地的替代性概念[18]。
自20世纪50年代逐渐形成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化管理,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为中国自然保护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也滋长了制度惰性,造成了法治困顿。2006年,全国人大主导的体系化自然保护地立法的探索,既是一种1994年以来国家实施《21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的、有益的中国式实践,也是一种试图以立法推动自然保护地从类型化管理向体系化发展的自上而下的法治变革尝试。这一努力因触及自然保护地管理和保护中部门之间、央地之间基于自然资源资产关系的利益冲突与平衡的核心问题而无果而终。这更说明,坚持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发展的改革及其法治化建设,需要更坚定和更强大的政治意愿及国家意志的支撑。
四、 中国自然保护地法治现代化建设展望
2013年后,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发展及其管理体制改革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目标领域,其基本策略就是创建新型的国家公园类型及其管理体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行分级、统一管理,保护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同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提出以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为目的,以实现重要自然生态资源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坚持问题为导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随后,在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九省市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改革现行各部门分头治理的自然保护地体制,开展保护地功能重组、合理界定国家公园范围,对国家公园实行更严格的保护,规定中央政府对部分国家公园直接行使所有权。
2017年9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正式发布,为国家公园试点提供了正式的规范性依据。同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要求:“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9]201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将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农业部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同年4月,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同年5月,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职责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整体移交国家公园管理局。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完成了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的机构设置,自然保护地统一监督管理机构的改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年9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制定《国家公园法》纳入二类立法项目。
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以后,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强调,创新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实施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提出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还提出了“到2025年,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法规、管理和监督制度”的总目标,以及“到2035年,显著提高自然保护地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自然保护地规模和管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18%以上”。该规范性文件表明,中国统一的综合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制度设计已经初步完成[20],这为中国自然保护地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管理基础和前提。
2020年以后,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进入新纪元,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从类型扁平化发展向以国家公园体制为导向的体系化发展转变。
2020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改革验收工作顺利完成,并开展了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与生态保护红线保持衔接、制定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等工作⑱。202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⑲。之后,自然资源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均将《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列为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重点项目,统筹推进制定工作。2022年,自然资源部《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完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管理制度,研究修改《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同年10月,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报送的《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同年11月,自然资源部审议通过《国家公园法(草案)》(送审稿),之后将由国务院审议决定是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展望未来,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的工作重心又到了重要的历史性节点:通过制定和实施自然保护地的国家综合性法律,实现中国自然保护地保护和管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促进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前,《国家公园法》已经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但《自然保护地法》尚未列入。就法体系构建和立法技术而言,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的重点在于需首先明确自然保护地的立法体系以及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这是制定自然保护地管理和保护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的前置性、基础性问题。对此,国家公园管理局研究确定了“两法+两条例+N办法”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框架,提出了构建“以《自然保护地法》为基本法律、《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支撑、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体系”方案,“确定了《自然保护地法》与《国家公园法》同步推进的原则”[21]。可见,在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中何者处于基本法地位的问题上,国家公园管理局持支持《自然保护地法》的立场。
然而,对于这一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学者们则有不同观点。法典化倡议者主张由《环境法典》中的“生态自然保护篇”担任基本法⑳,广义保护地体系倡导者主张制定《自然保护法》[22]。 笔者认为,这些方案皆具一定的合理性,但更能反映中国自然保护地法治理论和实践,并能抓住宝贵的国家立法资源和机遇的方案,应该是制定《国家公园体制法》,由其担当调整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本法。
《国家公园体制法》与目前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国家公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共同之处在于,《国家公园体制法》作为基本法,必然会调整和规范新的、独立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国家公园”。但《国家公园体制法》与《国家公园法》还存在本质区别,“国家公园”从创生起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保护地类型,而是带着体制改革使命和“整合职能”[23],因此,关于国家公园的国家立法不能将国家公园仅仅作为一个类型的自然保护地进行立法,而应当超越类型化发展的局限,展现“国家公园”的改革属性和功能,即国家公园体制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整体性改革。这样的一个关于国家公园的国家立法,其实质是《国家公园体制法》,是一项反映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发展和法治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法,将全面规范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为实现双重体制改革目标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因此,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应当紧紧抓住全国人大已经将《国家公园法》纳入立法规划的历史机遇,适当调整立法路线,将制定《国家公园法》转变为制定《国家公园体制法》,而不再重复制定《自然保护地法》。
回顾60多年发展历程,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经历了卓有成效的类型化发展阶段,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更迎来了体系化发展的治理升华。在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和人与生物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法治能够保障预期使命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然保护地的法治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蓝图中一道最亮丽的绿色风景线。
注释:
①由马骧聪主编、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的《环境资源法》第十一章“特殊环境资源保护法”中设“第三节 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法”“第四节 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法”“第五节 森林公园保护管理法”“第六节 自然遗迹和人文遗迹保护管理法”。参见:马骧聪主编的《环境资源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②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自然保护区达到2 740处,其中33处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46处自然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35处自然保护区同时划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200多处自然保护区被列为生态文明和环境科普方面的教育基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③这些国家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等。④其他涉及自然保护区规定的行政法规还有《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⑤其他重要规章还包括《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组织工作制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等。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名胜风景区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年)。⑦主要有:《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规定》《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风景名胜区分类标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办法》《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等。⑧2016年,原国家林业局对2012年度批准设立的18处国家级森林公园开展集中检查,重点检查了5年来这18处国家级森林公园机构建设、人员落实、总体规划编制、建设发展成效、旅游产品打造、保障机制建立等方面的工作。参见:张红梅等的《2016森林公园十件大事》,网址为http://www.gov.cn/xinwen/2017-02/07/content_5166122.htm。⑨例如,《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标准》《国家地质公园验收标准》《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开展国家地质公园监督检查的通知》等。⑩督察员由原国土资源部派出,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监督国家地质公园的相关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有关国际专家检查世界地质公园。原国土资源部每三年对国家地质公园展开一次评估工作,评估依据是各国家地质公园的年度报告、督察员报告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核查结果。评估结果分为三个等级:优秀、达标、不达标,对优秀级别的国家地质公园实施奖励,对不达标的国家地质公园作出警告,并限期整改,问题严重的需整改达标后才能开园。对一些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公园,经审议和批准,取消其称号。参见:赵逊和赵汀的《地质公园发展与管理》,载于《地球学报》,2009年第3期,第305页。⑪其他一些重要的国务院政策性文件,如《“十三五”时期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均未明确相关规范语义。⑫截至2021年7月,中国已有56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包括5项文化景观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参见:李洁整理的《中国入列$\langle $ 世界遗产名录$\rangle $ 56处全名单一览》,载于《兰州晨报》,2021年7月29日。⑬其他如《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2016年)等。⑭云南通过了《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2016年)和《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2005年),湖南省通过了《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2011年),福建省通过了《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2002年)。⑮该部分信息来源于笔者掌握的一手资料。在这两个议案的审议阶段,笔者作为专家学者有幸多次受邀参与研讨。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总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0%,目前85%以上符合上述自然遗产条件的资源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世界自然遗产划定的核心区内,面积不会超过陆地国土面积的5%。因此,草案将自然遗产保护的“自然遗产区域”(而非“自然遗产地”)拟制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保护区域”。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委员会专家解焱女士为代表。参见:孙晨的《“自然保护地法”能否在调研10年后浮出水面?−专访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总协调员解焱博士》,载于《青海科技》,2013第2期,第17—19页。⑱参见:《自然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号)和《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内矿业权差别化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函〔2020〕861号)。⑲2021年10月12日,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习近平指出:“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⑳例如,研究、推动环境法法典编撰的吕忠梅课题组。 -
[1]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EB/OL]. (2019−06−26)[2022−11−28]. [2] 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召开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研究部署当前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EB/OL]. (2022−11−24)[2022−11−28]. [3] 唐芳林. 中国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特色与意义[EB/OL]. (2019−09−20)[2022−11−28]. [4] 王权典. 再论自然保护区立法基本问题−兼评《自然保护地法》与《自然保护区域法》之草案稿[J]. 中州学刊,2007(3):92—96. [5] 杨锐, 等.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前言. [6]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 纪念我国第一次国家公园研讨会召开五周年[EB/OL]. (2019−04−29)[2022−11−29]. [7] 吴楚才.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研究[M].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1: 1. [8] 胡炜霞,吴成基. 论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可持续发展[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6):29—33. [9] 许涛,田明中. 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研究进展与趋势[J]. 旅游学刊,2010(11):90. [10] 朱清,黄德林. 从立法上加强对自然遗产保护的若干建议[J]. 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5(10):91. [11] 孙佑海. 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好自然保护立法工作[J]. 环境保护,2006(21):26—30. [12] 王灿发. 国外自然保护区立法比较与我国立法的完善[J]. 环境保护,2006(21):73—78. [13] 沈兴兴,马忠玉,曾贤刚. 我国自然保护区资金机制改革创新的几点思考[J]. 生物多样性,2015,23(5):701. [14] 孔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主要保护地类型的空间关系与分布格局[D].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2015. [15] 梅凤乔. 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亟待完善体制[J]. 环境保护,2006(21):53. [16] 杨泉. 浅析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J]. 法制与社会,2013(2):151—153. [17] 王旦旦. 对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制保障的检讨与完善[J]. 法制与社会,2014(11):255—256. [18] 高利红,程芳. 我国自然遗产保护的立法合理性研究−兼评《自然遗产保护法》征求意见稿草案[J]. 江西社会科学,2012,32(1):153—162. [1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20] 唐小平,刘增力,马炜. 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规则与路径研究[J]. 林业资源管理,2020(1):1—10. [2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快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建议”复文(2021年第3017号)[EB/OL]. (2021−11−22)[2022−11−28]. html. [22] 杜群. 环境法体系化中的我国保护地体系[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2): 123—140, 206—207. [23] 杜群, 等. 中国国家公园立法研究[M].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8: 52—54. -
期刊类型引用(9)
1. 所翟,俞渃茜,李媛辉,徐基良. 基于实证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区地方立法问题检视和优化路径. 生物多样性. 2024(02): 165-17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王庆日,郎海鸥,仲济香,陈美景,张冰松,于潇. 2023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2024年展望. 中国土地科学. 2024(03): 92-104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刘超,邓琼,何俊燊. 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的逻辑与路径. 海峡法学. 2024(02): 18-3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4. 韩凌月,周书悦. 气候变化视角下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4): 85-9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5. 吴凯杰. 生态环境法典自然保护地制度构建研究. 法学. 2024(10): 178-19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6. 刘南,马子帆. 跨区域协同立法: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的法制创新.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4(06): 49-5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7. 张婷,蔡磊. 安顺市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路径——基于安顺市重点自然保护地调研. 林业科技通讯. 2024(10): 95-9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8. 廖彩舜. 国家公园地役权的立法选择与规范构造. 公民与法(审判版). 2024(11): 13-2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9. 褚福建,吕兰颂,朱文博,付娟,蒙永辉,刘瑞峰,赵琳,霍延虎. 新时期地质公园发展探讨——以山东省为例. 山东国土资源. 2023(09): 37-4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1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93
- HTML全文浏览量: 133
- PDF下载量: 36
- 被引次数: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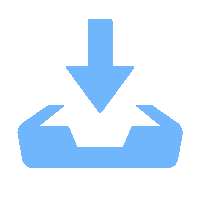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