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WANG P K C.Navigation strategies for multiple autonomous mobile robots moving in formation[J].Journal of Robotic System,1991,9(2):177-195.
|
| [2] |
丁衍,魏晨,鲍树语.基于一致性算法的时延多无人机编队分散化控制[J].计算机应用,2014,34(S1):151-155.DING Y,WEI C,BAO S Y.Formation control for multiple UAVs with time delay based on consensus algorithm[J].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2014,34(S1):151-155(in Chinese).
|
| [3] |
WEITZ L A,HURTADO J E,SINCLAIR A J.Decentralized cooperative-control design for multivehicle formations[J]. Journal of Guidance,Control,and Dynamics,2008,31(4):970-979.
|
| [4] |
KRISTIANSEN R,LORIA A,CHAILLET A,et al.Spacecraft relative rotation tracking without angular velocity measurements[J].Automatica,2009,45(3):750-756.
|
| [5] |
邵壮,祝小平,周洲,等.无人机编队机动飞行时的队形保持反馈控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5,33(1):26-32.SHAO Z,ZHU X P,ZHOU Z,et al.A formation keeping feedback control for formation flight of UAVs[J].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2015,33(1):26-32(in Chinese).
|
| [6] |
REN W,SORENSEN N.Distributed coordination architecture for multi-robot formation control[J].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2008,56(4):324-333.
|
| [7] |
REN W.Decentralization of virtual structure in formation control of multiple vehicle systems via consensus strategies[J].European Journal of Control,2008,14(2):1-11.
|
| [8] |
华思亮,尤优,张红,等.无人机编队的滚动时域控制[J].电光与控制,2012,19(3):1-5.HUA S L,YOU Y,ZHANG H,et al.Receding horizon control of UAV formations[J].Electronics Optics & Control,2012,19(3):1-5(in Chinese).
|
| [9] |
FAHIMI F.Non-linear model predictive formation control for groups of autonomous surface vessel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2007,80(8):1248-1259.
|
| [10] |
KEVICAKY T,BORRELLI F,FREGENE K,et al.Decentralized receding horizon 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of autonomous vehicle formations[J].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 Technologies,2008,16(1):19-33.
|
| [11] |
KHATIB O.Real-time obstacle avoidance for manipulators and mobile robo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otics Research,1986,5(1):290-298.
|
| [12] |
BALCH T,ARKIN R C.Behavior-based formation control for multirobot teams[J].IEEE Transaction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1998,14(6):926-939.
|
| [13] |
曹建福,凌志浩,高冲,等.基于群集思想的多智能体编队避障算法研究[J].系统仿真学报,2014,26(3):562-566.CAO J F,LING Z H,GAO C, et al.Obstacle avoidance and formation control for multi-agent based on swarming[J].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2014,26(3):562-566(in Chinese).
|
| [14] |
许敬刚,王宏伦,刘畅,等.无人机动态避撞区建模方法研究[J].电光与控制,2014,21(12):30-35.XU J G,WANG H L,LIU C,et al.Modeling of dynamic collision avoidance zone for UAVs[J].Electronics Optics & Control,2014,21(12):30-35(in Chinese).
|
| [15] |
LALISH E,MORGANSEN K A,TSUKAMAKI T.Formation tracking control using virtual structures and deconfliction[C]//Proceedings of the 45th 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2006. Piscataway, NJ:IEEE Press,2006:5699-5705.
|

 点击查看大图
点击查看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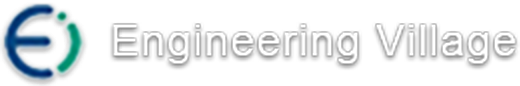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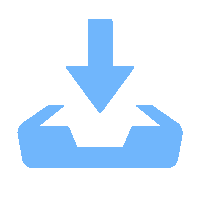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